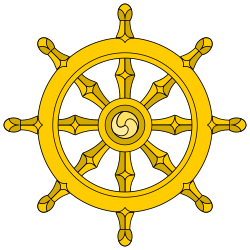Index
总导言
揭示教法的结构
尽管佛陀的教法高度系统化,但没有一部可归于佛陀的单一文本,其中他定义了法的架构,即他构建其具体教义表达的框架。在他漫长的弘法生涯中,佛陀根据不同的时机和情况以不同的方式教导。有时他会阐述教法核心的不变原则。有时他会调整教法以适应前来求教者的倾向和资质。有时他会根据需要特定回应的情况调整其阐述。但在流传至今被授权为“佛语”的文本结集中,我们找不到任何一部经,任何一篇开示,佛陀在其中将他教法的所有元素汇集起来,并将它们置于某个全面系统中的适当位置。
在以系统性思维为重的有文字的文化中,缺乏这样一部具有统一功能的文本可能会被视为一个缺陷,但在一个完全口传的文化中——正如佛陀生活和活动的文化——缺乏对法的描述性钥匙则几乎不被认为重要。在这种文化中,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不以概念的完整性为目标。老师不打算呈现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的学生也不渴望学习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学习过程——传承过程——中将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目标是实修、自我转化、真理的证悟,以及不动摇的心解脱。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教法总是为了方便而适应手头的情况。有时,佛陀会呈现更宏观的法景,将道的许多组成部分在一个分级或广泛的结构中统一起来。但是,尽管有几部开示展现了广阔的范围,它们仍然没有将法的所有元素都包含在一个总体的方案中。
本书的目的就是发展并例示这样一个方案。我在此尝试提供一幅佛陀教法的全景图,将各种经文融入一个有机的结构中。我希望这个结构能揭示佛陀阐述法背后的意图模式,从而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整个早期佛法的指南。我选取的经文几乎全部来自巴利语经藏的四个主要“部”或尼柯耶,但也包含了一些来自第五部《小部》中两本小书《自说》和《如是语》的文本。每一章都以其自身的导论开始,在其中我解释了文本所例示的早期佛法基本概念,并展示了这些文本如何表达这些思想。
我稍后将在本导论中简要提供关于尼柯耶的背景信息。但首先,我想概述我为组织这些经文而设计的方案。尽管我对这个方案的特定使用可能是原创的,但它并非纯粹的创新,而是基于巴利语义注对修习法所能带来的利益类型所做的三重区分:(1) 现世可见的福祉与快乐;(2) 关系到来世的福祉与快乐;(3) 最终的善,即 Nibbāna(梵语:nirṿ̄a)。
三个前导章节旨在引出体现这一三重方案的章节。第一章是对佛陀出世之前人类状况的考察。也许这就是菩萨 (Bodhisatta)——未来的佛陀——住在兜率天,俯视大地,等待适当的时机降生并接受他最后一次出生时所看到的人类生活景象。我们看到一个世界,人类无助地被推向衰老和死亡;在这个世界里,他们被境遇所左右,以至于被身体的痛苦所压迫,被失败和不幸所击倒,因变化和衰败而焦虑恐惧。这是一个人们渴望和谐相处,但他们未被调伏的情绪却一再迫使他们违背自己的良知,陷入升级为暴力和大规模毁灭的冲突之中的世界。最后,从最广阔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有情众生被自身的无明和渴爱推动,从一生到下一生,在名为轮回 (saṃsāra) 的生死循环中盲目流转的世界。
第二章记述了佛陀降临此世。他作为“一人”出现,是出于对世间的慈悲,他的出现是“大光明之显现”。我们跟随他的入胎与诞生、出家与寻求觉悟、证悟法以及决定教导的故事。本章以他在波罗奈附近的鹿野苑对五位比丘——他最早的弟子——所作的初次开示结束。
第三章旨在概述佛陀教法的特点,并由此引申出学人应以何种态度来学习此教法。经文告诉我们,法(Dhamma)并非秘密或深奥的教法,而是一种“公开宣说时便会彰显”的教法。它不要求对权威经典、天人启示或绝无谬误的教条产生盲信,而是鼓励探究,并以亲身实证作为判断其有效性的最终标准。此教法关注的是苦的生起与寂灭,而这可以在个人自身的体验中被观察到。它甚至不将佛陀树立为无可指摘的权威,而是鼓励我们去检验他,以确定他是否完全值得我们信赖与依靠。最后,它提供了一套循序渐进的方法,我们可以借此检验此教法,并通过这样做,为我们自己亲证究竟的真理。
从第四章开始,我们接触到的经文,是关于佛陀教法旨在带来的三种利益中的第一种。这被称为“此生的福祉与快乐”(diṭṭhadhamma-hitasukha),即在家庭关系、谋生方式和社群活动中遵循道德规范所带来的快乐。尽管早期佛法常被描绘为一种指向超验目标的彻底出离的修行,但《尼柯耶》揭示出佛陀是一位慈悲而务实的导师,他致力于促进一种社会秩序,使人们能够根据道德准则和平、和谐地共同生活。早期佛法的这一方面,在佛陀关于子女对父母的责任、夫妻间的相互义务、正命、统治者对臣民的责任,以及社群和谐与尊重的原则等教法中显而易见。
佛陀教法所导向的第二种利益是第五章的主题,称为“来世的福祉与快乐”(samparāyika-hitasukha)。这是通过积累福德,从而在未来生中获得善趣再生和成功的快乐。“福德”(puñña)一词指的是善业(kamma)(梵语:karma),从业能在轮回中产生有利果报的能力来看。本章我以一组关于业与再生教法的经文为开篇。接着是关于福德概念的一般性经文,然后是佛陀在经中所认可的三种主要“福德之基”的选文:布施(dāna)、持戒(sīla)和禅修(bhāvanā)。由于禅修在第三种利益中占有重要地位,这里作为福德之基所强调的禅修种类,是能产生最丰盛世间果报的禅修,即四梵住(brahmavihāra),特别是慈心的培育。
第六章是过渡章节,旨在为后续章节铺路。在展示其教法的修习确实有助于在世俗生活范畴内获得快乐与好运的同时,为了引导人们超越这些范畴,佛陀揭示了所有有为存在的危险与不足。他指出了感官之乐的缺陷、物质成功的短处、死亡的必然性,以及所有有为存在界的无常。为了在弟子心中激起对究竟善——涅槃(Nibbāna)的向往,佛陀再三强调轮回(saṃsāra)的危險。因此,本章以两篇极具震撼力的经文作结,详述了系缚于生死轮回之中的痛苦,从而将内容推向高潮。
接下来的四章致力于阐述佛陀教法旨在带来的第三种利益:究竟善(paramattha),即证得涅槃(Nibbāna)。其中第一章,即第七章,对解脱之道作了总体概述,通过对八正道各道支的定义进行分析性阐述,并通过对比丘训练的记述进行动态性阐述。一篇关于次第之道的长经,从比丘最初进入出离生活开始,直至其证得最终目标——阿罗汉果,综述了僧伽的训练过程。
第八章专注于调伏内心,这是僧伽训练中的主要重点。我在这里呈现的经文讨论了修心的障碍、克服这些障碍的方法、不同的禅修方法,以及当障碍被克服、弟子对心获得掌控时所要证得的境界。在本章中,我介绍了奢摩他(samatha)与毗婆舍那(vipassanā)的区别,即止与观,前者导向定(samādhi)或专注,后者导向慧(paññā)或智慧。然而,我收录的经文仅从产生观智的方法角度来论述观,而非其具体内容。
第九章,题为“点亮智慧之光”,探讨观智的内容。对于早期佛法,乃至几乎所有佛教宗派而言,观智或智慧是解脱的主要工具。因此,在本章中,我重点关注佛陀关于那些对开发智慧至关重要主题的教法,如正见、五蕴、六根、十八界、缘起以及四圣谛。本章结尾选录了数篇关于智慧的最终目标——涅槃(Nibbāna)的经文。
最终的目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一系列阶位,将一个凡夫转变为阿罗汉,即一位解脱者。因此,第十章“实证的诸阶位”,提供了一组关于此道途中主要阶位的经文。我首先将这一系列阶位作为一个渐进的序列来呈现;然后我回到起点,审视此进程中的三个主要里程碑:入流、不还者阶位以及阿罗汉果。最后,我以一组关于佛陀的经文作结,他是阿罗汉中的最上首者,在此处以他最常用来指代自己的称号——如来(Tathāgata)来称呼。
《尼柯耶》的起源
如上所述,我用来充实我的纲要的经文,全都选自《尼柯耶》(Nikāyas),即巴利三藏中的主要经集。有必要对这些文献的起源和性质作些说明。
佛陀没有写下他的任何教法,他的弟子们也没有将他的教法以文字记录下来。佛陀在世时的印度文化仍以口传为主。1 佛陀在恒河平原的城镇间游行,教导他的比丘和比丘尼,向成群前来听他说法的居士们讲道,回答好奇的询问者的问题,并与社会各阶层的人进行讨论。我们所拥有的他的教法记录,并非出自他本人的笔下,也不是由那些亲闻他教法的人所作的抄录,而是来自他般涅槃(parinibbāna)——即他入于涅槃(Nibbāna)——之后,为保存其教法而举行的僧伽结集。
这些结集所产生的教法,不太可能逐字逐句地复述了佛陀的话。佛陀必定是即兴说法,并根据那些寻求他指导之人的不同需求,以无数种方式阐述他的主题。通过口头传承来保存如此浩瀚且多样的材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将教法塑造成适合保存的格式,负责经文的僧人们必须对其进行整理和编辑,使其更适合于聆听、记忆、背诵、记诵和复述——这是口头传承的五个主要要素。这个过程可能在佛陀生前就已经开始,它会导致待保存材料在相当程度上被简化和标准化。
在佛陀住世期间,经文根据文学体裁被分为九类:sutta(散文经)、geyya(散文与偈颂混合体)、veyyākaraṇa(问答)、gāthā(偈颂)、udāna(自说语)、itivuttaka(如是语)、jātaka(本生故事)、abbhutadhamma(希有法)和 vedalla(抉择)。2 在他逝世后的某个时候,这种旧的分类系统被一种新的方案所取代,该方案将经文编排成更大的集合,在南传上座部佛教传统中称为《尼柯耶》(Nikāyas),在北印度佛教部派中称为《阿含》(Āgamas)。3 《尼柯耶-阿含》方案究竟何时成为主流尚不确定,但一旦它出现,就几乎完全取代了旧的系统。
《小品》(Cullavagga)是巴利《律藏》中的一部,记述了在佛陀般涅槃三个月后举行的第一次佛教结集中,权威经文是如何被汇编的。根据这份报告,佛陀圆寂后不久,僧团(Saṅgha)的实际领袖大迦叶长老(Mahākassapa)挑选了五百名比丘,他们全是阿罗汉或解脱者,共同集会,汇编了一个权威版本的教法。这次结集发生在雨季安居期间,地点是王舍城(Rājagaha)(现代的Rajgir),当时中印度最强大的国家摩揭陀国(Magadha)的首都。4 大迦叶首先请求在戒律方面最权威的优婆离尊者(Upāli)诵出律(Vinaya)。基于这次诵出,律藏(Vinaya Piṭaka),即《戒律总集》,得以汇编而成。然后,大迦叶请求阿难尊者(Ānanda)诵出“法”(Dhamma),即诸经,基于这次诵出,经藏(Sutta Piṭaka),即《经文总集》,得以汇编而成。
《小品》记载,当阿难尊者诵出《经藏》时,《尼柯耶》的内容与现今相同,诸经的排列顺序也与现今巴利三藏中的一样。这种叙述无疑是通过后期的视角来记录过去的历史。南传上座部以外的佛教部派的《阿含经》,与主要的四部《尼柯耶》相对应,但它们对经文的分类不同,其内容编排顺序也与巴利《尼柯耶》不同。这表明,如果《尼柯耶-阿含》的编排确实始于第一次结集,那么那次结集尚未将诸经在此方案中确定其位置。另一种可能是,此方案产生于更晚的时期。它可能产生于第一次结集之后、但在僧团分裂为不同部派之前的某个时间点。如果它产生于部派分裂的时代,它可能是由一个部派引入,然后被其他部派借鉴,因此不同的部派会将他们的经文置于该方案中的不同位置。
尽管《小品》关于第一次结集的记述可能包含了传说与史实的混合,但似乎没有理由怀疑阿难尊者在保存经文方面的作用。作为佛陀的侍者,阿难尊者从佛陀及其他大弟子那里学得了经文,将它们记在心中,并教给他人。在佛陀住世期间,他因其记忆力而受到赞扬,并被任命为“多闻第一”(etadaggaṃ bahussutānaṃ)。5 可能很少有比丘的记忆力能与阿难尊者相媲美,但在佛陀住世期间,个别比丘必定已经开始专攻特定的经文。材料的标准化和简化有助于记忆。一旦经文被分类为《尼柯耶》或《阿含》,保存和传承经文遗产的挑战就通过将经文专家组织成专门负责特定经集的团体来解决。僧团内的不同团体因此可以专注于记忆和解释不同的经集,整个僧团也可以避免对个别比丘的记忆力提出过高要求。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教法得以在接下来的三四百年里持续传承,直到最终被书写下来。6
在佛陀圆寂后的几个世纪里,僧团因戒律和教义问题而分裂,直到佛陀般涅槃后第三个世纪,至少出现了十八个部派佛教。每个部派可能都有自己或多或少被视为经典的经文集,尽管几个关系密切的部派可能共享同一套权威经文。虽然不同的佛教部派可能以不同方式组织其经集,虽然他们的经文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个别经文往往非常相似,有时几乎完全相同,它们所描绘的教义和修行也基本相同。7 部派之间的教义分歧并非源于经文本身,而是源于经文专家强加于其上的解释。在对立的部派用表达其独特教义立场的论著和义注将其哲学原则形式化之后,这些分歧变得更加固化。据我们所能确定,这些精微的哲学体系对原始经文本身的影响微乎其微,各部派似乎不倾向于为了迎合其教义议程而操纵经文。相反,他们通过义注,努力以一种能引申出支持其自身观点的方式来解释经文。这类解释显得辩护性和矫揉造作,为反对原始经文本身而辩解,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巴利三藏
可悲的是,当印度佛教在十一和十二世纪被入侵北印度的穆斯林摧毁时,大多数早期主流印度佛教部派的经典集都遗失了。这些入侵有效地为佛教在其发源地敲响了丧钟。只有一个早期印度佛教部派的完整经文集得以完整幸存下来。这就是用我们所知的巴利语保存下来的经文集。这个经文集属于古老的南传上座部,该部派于公元前三世纪被移植到斯里兰卡,因此得以逃脱在母国对佛教造成的浩劫。大约在同一时期,南传上座部也传播到东南亚,并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在该地区占据主导地位。
巴利三藏是南传上座部视为佛语(buddhavacana)的经文集。这部经文集的经文作为一个单一的经典得以幸存,并不意味着它们都可以追溯到同一时期;也不意味着构成其最古老核心的经文必然比其他佛教部派的对应经文更古老,后者中有许多以汉译或藏译的形式作为整个藏经的一部分幸存下来,或在少数情况下,作为另一种印度语言的独立经文幸存。尽管如此,巴利三藏对我们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至少有三个原因。
首先,它是一个完全属于单一学派的完整经集。尽管我们可以在三藏的不同部分之间察觉到历史发展的清晰迹象,但这种与单一学派的一致性赋予了经文一定程度的统一性。在源自同一时期的经文中,我们甚至可以说其内容具有同质性,在教义的多种表达方式背后,有一种单一的风味。这种同质性在四部《尼柯耶》和第五部《尼柯耶》的较早部分最为明显,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这些经文——考虑到前面提到的限定,即它们在其他已灭绝的佛教部派中有对应经文——我们已经触及了可发现的最古老的佛教文献层。
其次,整个经集都以一种中古印度-雅利安语保存下来,这种语言与佛陀本人所说的语言(或更可能是各种地方方言)关系密切。我们称这种语言为巴利语,但这个语言的名称实际上是源于一个误解。巴利(pāli)这个词本意是“文本”,即区别于义注的经典文本。义注家们将保存经典的语言称为 pālibhāsā,即“文本的语言”。在某个时候,这个词被误解为“巴利语”,一旦这个误解产生,它就根深蒂固,一直沿用至今。学者们认为这种语言是一种混合语言,显示了公元前三世纪左右几种普拉克里特方言的特征,并经过了部分梵语化的过程。8 虽然这种语言与佛陀本人可能说过的任何语言都不相同,但它属于与他可能使用过的语言相同的广泛语系,并源于相同的概念母体。因此,这种语言反映了佛陀从他所诞生的更广泛的印度文化中继承的思想世界,所以它的词语捕捉了那个思想世界的微妙细微之处,而没有外来影响的介入,即使在最好、最严谨的翻译中,这种介入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与经文的汉译、藏译或英译形成对比,后者会回响着从目标语言中选择的词语的内涵。
巴利三藏具有特殊重要性的第三个原因是,这个经集对于一个当代的佛教宗派具有权威性。与早期佛教已灭绝宗派的经文集纯粹具有学术意义不同,这个经集仍然充满生命力。它激励着从斯里兰卡、缅甸和东南亚的村庄与寺院,到欧洲和美洲的城市与禅修中心的数百万佛教徒的信仰。它塑造他们的理解,在面对困难的道德选择时指引他们,为他们的禅修实践提供信息,并为他们提供解脱之观智的钥匙。
巴利三藏通常被称为《三藏》(Tipiṭaka),即“三个篮子”或“三个总集”。这种三分法并非南传上座部独有,而是在印度佛教各部派中普遍使用,作为对佛教经典进行分类的一种方式。即使在今天,汉译保存的经文也被称为汉文大藏经。巴利三藏的三个总集是:1. 律藏(Vinaya Piṭaka),即《戒律总集》,包含了为指导比丘和比丘尼而制定的规则,以及为僧团的和谐运作而规定的规章。2. 经藏(Sutta Piṭaka),即《经文总集》,包含了佛陀及其主要弟子的经文、开示,以及偈颂形式的启发性作品、偈颂叙事和某些具有义注性质的作品。3. 论藏(Abhidhamma Piṭaka),即《哲学总集》,是七部论著的集合,它们对佛陀的教法进行了严谨的哲学系统化。
《论藏》显然是佛教思想演变后期阶段的产物,晚于另外两藏。《巴利论藏》代表了南传上座部学派对早期教法进行系统化的尝试。其他早期学派显然有自己的《论藏》体系。说一切有部的体系是唯一一个其经典文本完整无缺地得以幸存的。其经典集,像巴利版本一样,也由七部论著组成。这些论著最初是用梵文写成的,但只有汉译本才完整保存下来。它们所定义的体系在表述和哲学上都与其南传上座部的对应体系有显著不同。
《经藏》包含了佛陀的经文和讨论的记录,由五个称为《尼柯耶》(Nikāyas)的集合组成。在义注家时代,它们也被称为《阿含》(Āgamas),就像它们在北方佛教中的对应物一样。四个主要的《尼柯耶》是:1. 《长部》(Dīgha Nikāya):长篇经文的集合,三十四部经,分为三品(vaggas)或书。2. 《中部》(Majjhima Nikāya):中篇经文的集合,一百五十二部经,分为三品。3. 《相应部》(Saṃyutta Nikāya):相应经文的集合,近三千部短经,分为五十六个章节,称为相应(saṃyuttas),这些相应又被汇集为五品。4. 《增支部》(Aṅguttara Nikāya):数字经文的集合(或者可能是“递增经文”),约2400部短经,分为十一章,称为集(nipātas)。
《长部》和《中部》,乍看之下,似乎主要是根据长度来确立的:较长的经文归入《长部》,中等长度的经文归入《中部》。然而,对其内容的仔细列表分析表明,这两个经集之间的区别可能还有另一个因素。 《长部》的经文主要面向大众听众,似乎旨在通过展示佛陀及其教义的优越性来吸引潜在的皈依者。 《中部》的经文则主要面向佛教僧团内部,似乎旨在让新受戒的比丘熟悉佛教的教义和修行。9 这些实用目的是否是这两部《尼柯耶》背后的决定性标准,还是主要标准是长度,而这些实用目的只是它们各自长度差异的附带结果,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相应部》是按主题组织的。每个主题都是将诸经连接成一个相应或章节的“轭”(saṃyoga)。因此该经集的标题是“相应(saṃyutta)的经文”。第一品,《有偈品》,其独特之处在于它是根据文学体裁汇编的。它包含散文与偈颂混合的经文,按主题分为十一章。其他四品各包含处理早期佛教主要教义的长章节。第二、三、四品各自以一个致力于重要主题的长章节开篇,分别是:缘起(第12相应:因缘相应(Nidānasaṃyutta));五蕴(第22相应:蕴相应(Khandhasaṃyutta));以及六内外处(第35相应:六处相应(Saḷāyatanasaṃyutta))。第五部分处理主要的训练要素组,在后经典时期,这些要素被称为三十七道品(bodhipakkhiyā dhammā)。这些包括八正道(第45相应:道相应(Maggasaṃyutta))、七觉支(第46相应:觉支相应(Bojjhaṅgasaṃyutta))和四念住(第47相应:念住相应(Satipaṭṭhānasaṃyutta))。从其内容我们可以推断,《相应部》旨在服务于僧团内的两个群体。一个由教义专家组成,即那些寻求探索法的深层含义并为他们在宗教生活中的同伴阐明这些含义的比丘和比丘尼。另一个则由那些致力于观禅培育的人组成。
《增支部》是根据一种源于佛陀教学方法独特特征的数字方案来编排的。为了便于理解和记忆,佛陀经常以数字集的形式来阐述他的经文,这种格式有助于确保他所传达的思想能够轻易地记在心中。《增支部》将这些数字经文汇集成一部庞大的著作,共十一章(nipātas),每一章代表构成经文框架的术语数量。因此,有《一集》(ekakanipāta)、《二集》(dukanipāta)、《三集》(tikanipāta),以此类推,直到并结束于《十一集》(ekādasanipāta)。由于各种道支组已被收录在《相应部》中,《增支部》便可以专注于那些未被纳入重复集合的训练方面。《增支部》包含了相当一部分针对在家追随者的经文,处理世俗生活中的道德和修行问题,包括家庭关系(夫妻、子女与父母)以及获取、储蓄和使用财富的正确方式。其他经文则涉及比丘的实际训练。这部经集的数字编排使其特别方便于正式教学,因此长老比丘在教导弟子时,以及布道者在向在家人讲经时,都可以很方便地加以利用。
除了四个主要的《尼柯耶》外,巴利《经藏》还包括第五部《尼柯耶》,称为《小部》(Khuddaka Nikāya)。这个名字意为“小集”。也许它最初仅由一些无法被纳入四个主要《尼柯耶》的次要作品组成。但随着几个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品被创作并加入其中,其篇幅不断膨胀,直到成为五部《尼柯耶》中篇幅最大的一部。然而,《小部》的核心是一些简短作品的小集合,它们要么完全由偈颂构成(即《法句经》、《长老偈》和《长老尼偈》),要么由散文和偈颂混合构成(《经集》、《自说语》和《如是语》),其风格和内容表明它们非常古老。 《小部》的其他文本——例如《无碍解道》和两种《义释》——代表了南传上座部的立场,因此必定是在部派佛教时期,即早期学派走上各自教义发展道路时创作的。
巴利三藏的四部《尼柯耶》在汉文大藏经的《阿含经》中有对应部分,尽管这些来自不同的早期部派。与它们各自对应的是《长阿含经》,可能源于法藏部,最初由一种普拉克里特语翻译而来;《中阿含经》和《杂阿含经》,均源于说一切有部,由梵文翻译而来;以及《增一阿含经》,对应于《增支部》,通常被认为属于大众部的一个分支,并由一种中古印度-雅利安方言或一种混合了梵文元素的普拉克里特语方言翻译而来。汉文大藏经中还包含了来自这四个经集的个别经文的翻译,可能来自其他未确认的部派,以及来自《小集》的个别书籍的翻译,包括两个《法句经》的译本(据说其中一个非常接近巴利版本)和《经集》的部分内容,后者作为一个统一的作品,在汉译中并不存在。10
关于风格的说明
巴利经文的读者常常对文本的重复性感到烦恼。很难说这其中有多少源于佛陀本人——他作为一位游行布道者,必定会使用重复来强调他的观点——又有多少是由于结集者的原因。然而,很明显,高比例的重复性源于口头传承的过程。
为了在翻译中避免过度的重复,我不得不大量使用省略。在这一点上,我遵循了巴利文本的印刷版本,它们也经过了高度删节,但一部面向当代读者的译作需要更多的压缩,否则就有惹怒读者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一直热切地希望,通过删节,原文的任何本质内容,包括其韵味,都不会丢失。对读者的体谅和对文本的忠实,这两个理想有时会对译者提出相反的要求。
在翻译巴利经文时,处理对一组项目作出相同陈述的重复模式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例如,在翻译一部关于五蕴的经文时,人们很想放弃对各个蕴的列举,而将该经文变成一个关于蕴作为一个整体的一般性陈述。在我看来,这种方法有将翻译变成意译的风险,从而失去太多原文的韵味。我的总方针是,对该组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成员作完整陈述的翻译,而中间的成员仅用省略号隔开列举。因此,在一部关于五蕴的经文中,我只对色和识作完整的陈述,中间则有“受……想……行……”,以此暗示完整的陈述同样适用于它们。
这种方法需要频繁使用省略号,这种做法也招致批评。当遇到叙述框架中的重复段落时,我有时会将其浓缩,而不是用省略号来显示文本被省略的地方。然而,对于阐述教义的文本,我坚持前一段所述的做法。我认为译者有责任,在翻译具有教义意义的段落时,准确地显示出文本被省略的地方,而对此,省略号仍然是手头最好的工具。
注释
-
佛陀在世的确切年代在学者中仍有争议。直到最近,最常被引用的数字是公元前566-486年,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印度学家开始质疑这些数字,目前倾向于将他的逝世时间定在公元前400年左右。 ↩
-
参见,例如,MN 22.10 (I 133)。其中一些术语晦涩难懂,义注师们似乎费力地寻找方法来确定属于其范畴的文本。 ↩
-
但即使晚至义注师时代(公元五世纪),上座部传统也称它们为Āgamas(阿含)和Nikāyas(尼柯耶)。 ↩
-
《小品》中关于第一次结集的记载见于 Vin II 284–87。雨安居(vassāvāsa)是一个为期三个月的时期,与印度的雨季相吻合,期间佛教比丘必须停止游方,留在固定的住所。安居通常从七月月圆日的次日持续到十月月圆日。 ↩
-
见向智长老(Nyanaponika)与何克(Hecker)所著的《佛陀的大弟子》(Great Disciples of the Buddha),第四章。 ↩
-
在上座部传统中,经典的文字记录发生于公元前一世纪的斯里兰卡。当时,比丘们担心口头传承的教法可能会失传,便集体将经文刻在贝叶上,并将其装订成册,这便是书籍的原型。在此之前,虽然个别比丘可能会为了帮助记忆而写下经文,但官方认可的教法抄本并不存在。关于经典的文字记录,见阿迪卡拉姆(Adikaram)的《锡兰早期佛教史》(Early History of Buddhism in Ceylon),第79页;以及马拉拉塞克拉(Malalasekera)的《锡兰的巴利文献》(The Pāli Literature of Ceylon),第44–47页。在印度,经典的文字记录可能比在斯里兰卡更早。 ↩
-
参见,例如,释明珠(Thich Minh Chau)的《汉译中阿含与巴利中部尼柯耶》(The Chinese Madhyama Āgama and the Pāli Majjhima Nikāya);以及宗舜(Choong Mun-keat/Wei-keat)的《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The Fundamental Teachings of Early Buddhism)。 ↩
-
关于巴利语的性质,见诺曼(Norman)的《巴利文献》(Pāli Literature),第2–7页。 ↩
-
见曼尼(Manné)的《巴利尼柯耶中的经的分类》(“Categories of Sutta in the Pāli Nikāyas”),特别是第71–84页。 ↩
-
以上信息源自宗舜的《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第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