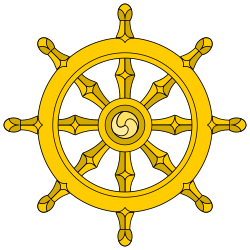Index
第十章:证悟的层次

导言
如我们所见,培育智慧的目标在于证悟涅槃。诸部《尼柯耶》规定了个人在证悟涅槃途中的一系列固定阶段。通过这些阶段,一个人从对法之真理盲目的“无闻凡夫”,演变为一位阿罗汉,即解脱者,他在今生已完全彻见四圣谛并证悟涅槃。本书前几章我已提及其中几个阶段。在本篇中,我们将更系统地探讨它们。
当进入通往涅槃的不可逆转之道时,人便成为一位圣者(ariyapuggala),这里的“圣”(ariya)一词意指精神上的高贵。圣者主要有四种类型。每个阶段又分为两个阶段:道(magga)及其果(phala)。1在道位阶段,据说此人正在为证悟某一特定果位而修行,并必定在同一生中证得;在果位阶段,据说此人已安住于该果位。因此,四种主要类型的圣者实际上包含四对或八种圣者。如第十章第一篇(1)所列,他们是:(1)为证悟入流果而修行者,(2)入流者,(3)为证悟一来果而修行者,(4)一来者,(5)为证悟不来果而修行者,(6)不来者,(7)为证阿罗汉果而修行者,(8)阿罗汉。第十章第一篇(2)根据他们诸根的相对强度将这八者分级,使得后一阶段者的诸根强于前一阶段者。前七种人统称为有学(sekhas),即处在更高阶训练中的弟子;阿罗汉则被称为无学(asekha),即超越训练者。
这四个主要阶段本身以两种方式定义:(1)通过通往相应果位的道所断除的烦恼来定义;(2)通过证得该特定果位者死后的归宿来定义。第十章第一篇(3)对这四种类型给出了标准定义,其中既提到了所断除的烦恼,也提到了他们未来的归宿。
诸部《尼柯耶》将被断除的烦恼归为一组十种结(saṃyojana)。入流者断除前三结:身见(sakkāyadiṭṭhi),即认为有一个真实存在的我,或与五蕴等同,或与五蕴有某种关系;对佛、法、僧及修行的疑(vicikicchā);以及戒禁取(sīlabbataparāmāsa),即相信仅凭外在的仪式,特别是宗教仪式和苦行,就能导向解脱。入流者确保最多再经历七次生命便可证得圆满觉悟,这七次生命都将发生在人界或天界。入流者绝不会有第八次生命,并且永远从三恶道——地狱、饿鬼界和畜生道——的再生中解脱。
一来者(sakadāgāmī)不会根除任何新的结。他或她已经断除了入流者所断除的三结,并进一步减弱了三种不善根——贪、瞋、痴——使其不常生起,且生起时也不会变得执着。2顾名思义,一来者将只再回到这个世界一次,然后终结苦。
不来者(anāgāmī)根除“五下分结”。也就是说,除了入流者所断除的三结外,不来者还根除了另外两结:欲贪和瞋恚。因为不来者已根除欲贪,他们没有束缚于欲界生命的结。因此,他们投生于色界(rūpadhātu),通常是在五个被称为“净居天”(suddhāvāsa)的天界之一,这些天界专为不来者再生而设。他们在那里证得最终的涅槃,永不返回欲界。
然而,不来者仍受“五上分结”所束缚:色界有欲、无色界有欲、我慢、掉举和无明。断除五上分结者,便再无任何束缚于缘起世间的结。他们就是阿罗汉,已断尽一切烦恼,并“通过最终的智慧而完全解脱”。
四类圣弟子(依所断之结与所剩再生类型)
弟子类别新断除的结剩余的再生类型
入流者
身见、疑、戒禁取
最多在人天中再生七次
一来者
无,但减弱贪、瞋、痴
在欲界再生一次
不来者
欲贪与瞋恚
在色界化生
阿罗汉
色界有欲、无色界有欲、我慢、掉举、无明
无
除了四类主要圣者,诸部《尼柯耶》有时还提到一对仅次于入流者的圣者——见第十章第一篇(3)。这两类——被称为法随行者(dhammānusārī)和信随行者(saddhānusārī)——实际上属于第八类圣弟子中的两种类型,即为证悟入流果而修行之人。诸部《尼柯耶》包含这对圣者,是为了表明在通往入流果的道上,可以根据其主导根而将弟子分为两类。法随行者是以慧为主导者,信随行者是以信为主导者。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个果位之前的这个阶段,只有信和慧,而非其他三根——精进、念、定——被用来区分不同类型的弟子,这可能具有重要意义。3
上述文本中对圣弟子类别的解释,摘自《蛇喻经》(中部22),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即所有达到这些阶段的人都是比丘。然而,情况绝非如此。《蛇喻经》的摘录之所以这样措辞,只是因为它针对的是比丘。第十章第一篇(4)纠正了这一印象,并更清晰地描绘了圣弟子的类别是如何分布于佛陀的追随者群体中的。作为一种恒常的状态,阿罗汉果位是为比丘和比丘尼保留的。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比丘和比丘尼才能证得阿罗汉果;经文和义注确实记载了一些居士证得最终目标的案例。然而,这些弟子要么在临终时证得阿罗汉果,要么在证果后很快就出家。他们不会继续作为在家的阿罗汉居士,因为居家生活与已断除一切渴爱者的状态是不相容的。
相比之下,不来者可以继续作为在家的居士生活。当他们继续作为居士生活时,他们已经根除了欲欲,因此必然持守梵行。他们被描述为“身着白衣,过着梵行生活的居士……随着五下分结的断除,将(在净居天)化生,并在那里证得最终的涅槃,永不从那个世界返回。”尽管经文没有明确说明,但可以合理推断,那些为证不来果而修行的弟子也持守全时梵行。然而,在家的入流者和一来者不一定持守梵行。在经中,佛陀将他们描述为“身着白衣,享受欲乐的居士……他们奉行我的教导,响应我的建议,已超越疑惑,摆脱困惑,获得无畏,并在导师的教法中不再依赖他人。”因此,虽然一些入流者和一来者可能持守梵行,但这绝不是这两类弟子的典型特征。
诸部《尼柯耶》偶尔采用另一种分类圣弟子的方案,该方案以主导根而非仅以证悟水平作为区分的基础。该方案的主要来源是《翅吒山经》中的一段,此处作为第十章第一篇(5)收录。这种分类方法将阿罗汉分为两类:俱解脱者(ubhatobhāgavimutta)和慧解脱者(paññāvimutta)。前者被称为“俱解脱”,因为他们通过对无色禅定的掌控而从色法中解脱,并通过证得阿罗汉果而从一切烦恼中解脱。那些“慧解脱”的阿罗汉并未掌控无色定,而是通过其智慧的力量结合低于无色界的定力而证得最终果位。
那些证得任何较低阶段——从入流果到包括阿罗汉道在内——的人被分为三类。“身证者”(kāyasakkhī)是处于这些阶段中任何一个阶段且已掌控无色定的人;“见至者”(diṭṭhippatta),是处于这些阶段中任何一个阶段但缺乏无色定且以智慧为主的人;“信解脱者”(saddhāvimutta),是处于这些阶段中任何一个阶段但缺乏无色定且以信为主的人。此类型学中的最后两人即是上文解释的法随行者和信随行者。
应当注意的是,该方案没有提及在入流道位上拥有无色定的人。这不应被理解为原则上排除了这种类型,而只是认为这种类型对于分类目的而言无关紧要。似乎在这个预备阶段,为在定力方面有卓越技能者单独设立一个类别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在文本选录中,我接下来将单独探讨主要类型。我从入流者开始,但首先需要一些初步说明。在诸部《尼柯耶》中,绝大多数人类被称为“无闻凡夫”(assutavā puthujjana)。无闻凡夫不尊重佛陀及其教法,对法没有理解,也未致力于修行。佛陀之道的目的是引导无闻凡夫证得不死,而证悟的各个阶段是完成此过程的步骤。这一转化过程通常始于一个人遇到佛陀的教法并对佛陀作为觉悟者生起信心。然后,他必须对法获得清晰的理解,受持戒律,并开始系统地修习此道。在经文中,这样的人在广义上被称为圣弟子(ariyasāvaka),而不必是在狭义的、技术的意义上指已经证得道与果的人。
后来的传承将对法有信心并渴望达到入流状态的人称为善凡夫(kalyāṇaputhujjana)。为了达到入流的证悟,有抱负的弟子应培育“入流四支”。如第十章第二篇(1)所解释,这些是:亲近贤善的善知识;听闻正法;仔细作意(例如,通过欲乐、过患和出离的方式);以及依法修行(通过受持戒、定、慧三学)。有抱负的弟子所进行的修行之巅峰是培育观智:彻底观照五蕴、六处和诸界为无常、与苦相连、且无实质的自我。在某个时刻,当观智达到顶峰时,弟子的理解将经历一次重大转变,这标志着他进入了“正性决定”,即真正不可逆转地导向涅槃的八正道。如第十章第二篇(2)所述,这样的弟子已从凡夫地升起,达到了圣者地。虽然尚未成为入流者,但处于此阶段的人在证得入流果之前不会去世。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证得圣道的弟子中,通过信而达到的称为信随行者,与通过慧而达到的称为法随行者,两者之间存在区别。但虽然信随行者和法随行者因其主导根而异,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必须进一步培育他们所进入的道。一旦他们知见法的本质——当他们“得法眼”并“彻见法”时——他们就成为入流者,注定在最多七次生命内达到完全觉悟并证得最终的涅槃;见第十章第二篇(3)。入流者根除前三结,并获得八正道的八个道支。他们还拥有“入流四支”:对佛、法、僧的已确证的信心,以及“圣者所喜悦的戒”,即坚定地遵守五戒;见第十章第二篇(4)-(5)。
见到法的真理后,入流者面临的挑战是培育此见,以断除剩余的烦恼。下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即证得一来者地,并不能完全断除任何烦恼。然而,它确实减弱了三种根烦恼——贪、瞋、痴——的程度,足以确保弟子将只再回到“这个世界”,即欲界一次,然后终结苦。
证得前两个阶段——入流者或一来者——的弟子不必停滞不前,而是可以向更高的两个阶段迈进。诸部《尼柯耶》中对证悟的描述表明,一个具有极其锐利诸根的善凡夫也可能直接晋升到不来者的阶段。不来者的状态总是被说成是通过断除五下分结而证得的,即入流者根除的三结,再加上欲贪和瞋恚。从诸部《尼柯耶》来看,似乎具有极其锐利智慧的人可以一举达到这个阶段。然而,义注解释说,在这种情况下,此人实际上是在极短时间内相继通过前两个道与果,然后才达到第三道与果。
根据第十章第三篇(1),为了断除五下分结,一位比丘首先证得四禅那之一或较低的三种无色定之一;第四无色定的构成要素过于微细,无法作为观智的所缘。他将注意力转向构成禅那或无色定的要素,4并将它们归入五蕴之下:即色(在涉及无色定时省略)、受、想、行、识。完成之后,他观照这些现已归类于五蕴的要素,带有三种特相:无常、苦、无我(扩展为十一个标题)。随着观照的深入,在某一时刻,他的心会从一切有为法中转向,专注于不死界——涅槃。如果他诸根锐利,能当场放下一切执着,他便证得阿罗汉果,断尽诸漏;但如果他尚不能舍弃所有执着,他便证得不来者的状态。
佛陀认识到个体在实现最终目标时所采取的方法存在差异,在第十章第三篇(2)中,他根据证悟的方式将人分为四类。这四类是通过两对组合得到的。他首先根据弟子诸根的强度进行区分。诸根强者在今生即证得最终涅槃。诸根相对较弱者在下一生证得最终涅槃,因此大概是以不来者的身份去世。另一对组合则根据他们的修行模式来区分弟子。一类采取“困难”的方法,使用能产生锐利智慧并直接导向厌离和离欲的禅修所缘。另一类则采取更平顺、更愉悦的途径,即通过四禅那。这两种类型大致对应于重观者和重止者。
《入流相应》中的一篇短经,即第十章第三篇(3),讲述了迪伽乌(Dīghāvu)的故事,他是一位通过强调观的困难途径达到不来者阶段的青年。迪伽乌临终躺在病床上时,佛陀来看望他,并请他修习入流四支。迪伽乌说他已经具备了这些要素,从而表明他是一位入流者。佛陀接着指示他培育“六种与真实知识相关的事物”。他显然听从了佛陀的建议,因为在他死后不久,佛陀宣布他已作为不来者去世。虽然迪伽乌可能已经证得禅那,因此不需要被教导其修习方法,但他也可能完全是通过这六种观照所生起的深邃观智而达到不来者阶段的。
第十章第三篇(4)对证得阿罗汉果和不来者阶段的人作了进一步的区分。这类经文指出了即使在同一精神层次的人之间也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正是因为佛陀能够做出这样的区分,他才被说成是拥有对众生诸根多样性的完美理解。
由于不来者已根除五下分结,他们不再受缚于欲界。然而,他们仍未完全从轮回中解脱,仍受五上分结所束缚:色界有欲、无色界有欲、“我是”我慢、微细的掉举,以及无明。“我是”(asmimāna)我慢不同于身见,即我见(sakkāyadiṭṭhi),尽管它与我见有部分相似之处。我见肯定一个恒存的我在五蕴相关中存在,或作为五蕴的同一体,或作为其内核,或作为其拥有者和主宰者。但“我是”我慢缺乏清晰的概念内容。它潜伏在心的底层,是一种模糊、无形但专横的“我”作为具体实体的感觉。尽管我见在入流阶段就已被断除,但“我是”我慢在圣弟子中甚至持续到不来者阶段。这便是敏锐的《差摩迦经》——第十章第四篇(1)——的要点,其中有两个优美的譬喻:花香和洗净的布。圣弟子与凡夫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认同“我是”我慢。他们认识到“我是”我慢仅仅是想象的产物,一个不指向自我、不指向真实存在的“我”的错误观念。但他们尚未完全克服它。
不来者身上持续存在的微细执着和残余的“我是”感都源于无明。为了走到道的尽头,不来者必须根除剩余的无明部分,并驱散所有贪爱和我慢的痕迹。当无明、贪爱和我慢被根除的关键时刻,标志着从不来者阶段向阿罗汉果的转变。两者之间的差异可能很微细,因此需要有区分它们的标准。在第十章第四篇(2)中,佛陀提出了几个标准,有学和阿罗汉可以据此确定各自的地位。其中一个特别有趣的标准涉及他们与五根的关系:信、精进、念、定、慧。有学以智慧见到诸根所趋向的目标——即涅槃——但不能安住于其中。阿罗汉以智慧见到最高目标,并且能够安住于该目标。
接下来的文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阿罗汉。第十章第四篇(3)用一系列譬喻来描述阿罗汉,并在同一段落中加以阐释。第十章第四篇(4)列举了阿罗汉不能做的九件事。在第十章第四篇(5)中,舍利弗(Sāriputta)尊者描述了阿罗汉在面对强大的感官对象时不动摇的心境,在第十章第四篇(6)中,他列举了阿罗汉的十力。第十章第四篇(7)是《界分别经》的节选,开头是关于通过观照诸界而证得阿罗汉果的记述;相关段落已作为第九章第四篇(3)(c)收录于前一章。接着,论述转向阿罗汉的“四依止”(catāro adhiṭṭhāna),这里称之为“寂静的牟尼”(muni santo)。第十章第四篇(8)是本节的最后一篇,是一首赞颂阿罗汉卓越品质的诗歌。
阿罗汉中首屈一指的是佛陀本人,本篇的最后一节即专门论述他。该节标题为“如来”,这是佛陀在提及自己作为解脱真理的发现者和带来者这一原型角色时使用的词语。这个词可以有两种解释:若作 tathā āgata,“如是而来”,则意指佛陀是遵循一个既定模式而来(义注将其解释为圆满十波罗蜜——pāramīs——和三十七道品);若作 tathā gata,“如是而去”,则意指他是遵循一个既定模式而去(义注将其解释为他通过圆满修习奢摩他、毗婆舍那、道与果而趋向涅槃)。
后期的佛教形式在佛与阿罗汉之间划出了极端的区别,但在诸部《尼柯耶》中,如果以后期文献为解释基准,这种区别并不如人们预期的那么明显。一方面,佛是一位阿罗汉,这一点从对世尊的标准礼敬偈(iti pi so bhagavā arahaṃ sammā sambuddho…)中可以明显看出;另一方面,阿罗汉是佛(buddha),意指他们通过觉悟佛陀本人所证悟的相同真理而获得了圆满的觉悟(sambodhi)。因此,恰当的区别在于一位正等正觉者(sammā sambuddha)与一位作为正等正觉者的声闻弟子(sāvaka)而获得觉悟和解脱的阿罗汉之间的区别。然而,为避免如此复杂的措辞,我们将采用通常的说法,将这种区别表述为佛与阿罗汉之间的区别。
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他们之间的区别主要是时间顺序上的,或许再加上一些正等正觉者特有的额外能力吗?还是他们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以至于应被视为不同的类型?诸部《尼柯耶》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有趣甚至引人遐思的模棱两可,如此处收录的文本所示。第十章第五篇(1)提出了关于“如来、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与“慧解脱比丘”之间区别的问题;显然,“慧解脱比丘”(bhikkhu paññāvimutta)这个表述在此处用于适用于任何阿罗汉弟子的意义上,而不仅仅是用于指那些缺乏无色定者(即,是包容性的意义,而非与俱解脱阿罗汉相对的慧解脱阿罗汉)。文本给出的答案从角色和时间优先性方面表达了这种区别。佛陀的功能是发现和阐述道,并且他对道的错综复杂有着其弟子所不具备的独特熟悉度。他的弟子们遵循他揭示的道,并在他的指导下随后证得觉悟。
后期佛教的论辩文献有时将佛陀描绘为由大悲心所驱动,而其阿罗汉弟子则冷漠疏远,对自己同胞的困境漠不关心。似乎是为了预先反驳这种批评,第十章第五篇(2)指出,不仅佛陀,阿罗汉以及仍在修行中的博学贤善的弟子,他们的出现都是为了许多人的福祉,他们出于对世间的悲悯而生活,并为了他们的同胞,包括天人和人类的利益、福祉和快乐而教导法。因此,如果将此文本视为权威,就不能声称悲悯和利他关怀是区分佛与阿罗汉的品质。
然而,第十章第五篇(3)就此问题给了我们另一个视角。在此,佛陀通过询问舍利弗(Sāriputta)尊者是否完全了知过去、现在和未来诸佛的戒行、品质(或许指定)、智慧、禅住和解脱,来挑战他的“狮子吼”。对此,这位大弟子只能回答否定。但舍利弗宣称,他知道三世诸佛都是通过舍弃五盖,将其心安住于四念住,并正确地培育七觉支而证得正等正觉的。
然而,这些是佛陀与阿罗汉弟子共同圆满的道之面向。除此之外,佛陀拥有某些品质,使他们超越了即使是最杰出的阿罗汉。从诸部《尼柯耶》来看,他们的优越性似乎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第一,他们的存在本质上是“为了他人”的,其方式即使是最具利他心的阿罗汉弟子也只能效仿而永远无法企及;第二,他们的知识和神通远大于阿罗汉弟子的。
佛陀指出,即使是内心完全解脱、拥有“无上知见、修行与解脱”的比丘,也依然敬重如来 (Tathāgata),因为他的觉悟能帮助他人觉悟,他的解脱能帮助他人获得解脱,他亲证的涅槃能使他人亲证涅槃(MN 35.26; I 235)。在第十章第五篇(4)中,我们看到两组被认为是佛陀的特殊禀赋,使他能够在集会中“作狮子吼”并转动法轮。这便是如来十力与四无所畏。尽管弟子也具备其中一些能力,但这两组特质合在一起,是佛陀所独有的,使他能根据众生各自的根性与性情来引导和教导他们。四无所畏赋予佛陀一种权威的胆识,一种唯有宗教创始者才能行使的宏大使命感。第十章第五篇(5)将如来比作日月,因为他出现于世,是伟大光明的显现,驱散了无明的黑暗。第十章第五篇(6)将他比作从灾难中拯救鹿群的人,以此描绘他为人类的伟大恩主。
在第十章第五篇(7)中,我们回到了前面介绍过的狮子吼的比喻,一个长篇譬喻将佛陀宣告普遍无常,比作狮子出窟时的吼声。如同初转法轮经的结尾段落(见第二章第五篇),这段经文也让我们注意到佛陀使命的宇宙性范畴。他的讯息不仅传达给人类,更上达至高天界,动摇了天神们的错见。
最后,第十章第五篇(8)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简短的解释,说明为何佛陀被称为如来 (Tathāgata)。他被称为如来,因为他已圆满觉悟了世间的本质、其集起、其寂灭,以及导向其寂灭之道;因为他已圆满彻见了世间的一切现象,无论是所见、所闻、所觉或所识;因为他的言说恒常真实;因为他言行一致;因为他在世间拥有至高无上的主导力。经文以一首充满启发的诗偈结尾,这可能是经文的编纂者附上的,诗中赞颂佛陀为世间至上的皈依处。
这段散文与诗偈所表达的对如来的个人虔敬,让我们接触到早期佛法中一股温暖的宗教情感,这股情感总是蕴藏在其冷静沉着的表象之下。这种宗教维度,使佛法不仅是一种哲学、一种伦理体系或一套禅修技巧。它从内在赋予佛法生命力,引领其追随者向上向善,使佛法成为一条完整的修行之道——一条根植于对一位特定人物之信心的道路,他既是解脱真理的至上导师,也是他所教导之真理的最卓越典范。
第一篇:世间的福田
(1)八种应供者
“诸比丘,此八种人应受供养、应受款待、应受布施、应受合掌致敬,是世间无上的福田。是哪八种呢?
“须陀洹,为证悟须陀洹果而修行者;斯陀含,为证悟斯陀含果而修行者;阿那含,为证悟阿那含果而修行者;阿罗汉,为证悟阿罗汉果而修行者。
“诸比丘,此八种人应受供养、应受款待、应受布施、应受合掌致敬,是世间无上的福田。”
(AN 8:59; IV 292)
(2)以根的差别区分
“诸比丘,有此五根。是哪五根呢?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此即为五根。
“圆满成就此五根者,是阿罗汉。若根力稍弱,是为证悟阿罗汉果而修行者;若再弱一些,是阿那含;若再弱一些,是为证悟阿那含果而修行者;若再弱一些,是斯陀含;若再弱一些,是为证悟斯陀含果而修行者;若再弱一些,是须陀洹;若再弱一些,是为证悟须陀洹果而修行者。
“但是,诸比丘,我说,完全且彻底不具备此五根的人,是‘局外人,立于凡夫之中’。”
(SN 48:18; V 202)
(3)于善说之法中
42. “诸比丘,我所善说的法,是清晰、开放、显明、无补缀的。于我所善说的、清晰、开放、显明、无补缀的法中,那些已断尽诸漏的阿罗汉比丘——已圆满梵行,所作已办,已卸重担,已达己利,已彻底断除有结,以究竟智而完全解脱——他们不再有轮回。5
43. “诸比丘,我所善说的法,是清晰……无补缀的。于我所善说的法中,那些已断除五下分结的比丘,都将化生于[净居天],在那里证得究竟涅槃,永不复还于此世。6
44. “诸比丘,我所善说的法,是清晰……无补缀的。于我所善说的法中,那些已断除三结,并减轻贪、瞋、痴的比丘,都是斯陀含,再来此世一次,便能终结苦。
45. “诸比丘,我所善说的法,是清晰……无补缀的。于我所善说的法中,那些已断除三结的比丘,都是须陀洹,不再受缚于下界,命运已定,以觉悟为归宿。7
46. “诸比丘,我所善说的法,是清晰……无补缀的。于我所善说的法中,那些随法行者或随信行者,都以觉悟为归宿。8
47. “诸比丘,我所善说的法,是清晰、开放、显明、无补缀的。于我所善说的法中,那些对我具足信心、具足爱敬的人,都以往生天界为归宿。”9
(出自 MN 22: Alagaddupama Sutta; I 140–42)
(4)教法的圆满性
6. “当一位比丘已断除渴爱,从根拔除,使其如断头棕榈树,令其灭尽,不再有未来生起之可能,那位比丘即是漏尽阿罗汉,已圆满梵行,所作已办,已卸重担,已达己利,已彻底断除有结,以究竟智而完全解脱。”
7. “除了乔达摩 (Gotama) 大师之外,是否有任何一位乔达摩大师的比丘弟子,于此生中,以亲身智证,证入并安住于那无漏的心解脱、慧解脱呢?”10
“婆蹉 (Vaccha),不只一百,或二、三、四、五百,而是有更多更多的比丘,我的弟子们,于此生中,以亲身智证,证入并安住于那无漏的心解脱、慧解脱。”
8. “除了乔达摩 (Gotama) 大师和诸比丘之外,是否有任何一位乔达摩大师的比丘尼弟子,于此生中,以亲身智证,证入并安住于那无漏的心解脱、慧解脱呢?”
“不只一百……或五百,而是有更多更多的比丘尼,我的弟子们,于此生中,以亲身智证,证入并安住于那无漏的心解脱、慧解脱。”
9. “除了乔达摩 (Gotama) 大师、诸比丘与比丘尼之外,是否有任何一位乔达摩大师的白衣男居士弟子,过着梵行生活,因断除五下分结,将化生于[净居天],在那里证得究竟涅槃,永不复还于此世呢?”11
“不只一百……或五百,而是有更多更多的男居士,我的弟子们,身着白衣,过着梵行生活,因断除五下分结,将化生于[净居天],在那里证得究竟涅槃,永不复还于此世。”
10. “除了乔达摩 (Gotama) 大师、诸比丘与比丘尼,以及过着梵行生活的白衣男居士之外,是否有任何一位乔达摩大师的白衣男居士弟子,受用欲乐,但遵行他的教导,回应他的劝告,已超越疑惑,远离困惑,获得无畏,于导师的教法中,不再依赖他人?”12
“不只一百……或五百,而是有更多更多的男居士,我的弟子们,身着白衣,受用欲乐,但遵行我的教导,回应我的劝告,已超越疑惑,远离困惑,获得无畏,于导师的教法中,不再依赖他人。”
11. “除了乔达摩 (Gotama) 大师、诸比丘与比丘尼,以及不论是过着梵行生活或受用欲乐的白衣男居士之外,是否有任何一位乔达摩大师的白衣女居士弟子,过着梵行生活,因断除五下分结,将化生于[净居天],在那里证得究竟涅槃,永不复还于此世呢?”
“不只一百……或五百,而是有更多更多的女居士,我的弟子们,身着白衣,过着梵行生活,因断除五下分结,将化生于[净居天],在那里证得究竟涅槃,永不复还于此世。”
12. “除了乔达摩 (Gotama) 大师、诸比丘与比丘尼,以及不论是过着梵行生活或受用欲乐的白衣男居士,和过着梵行生活的白衣女居士之外,是否有任何一位乔达摩大师的白衣女居士弟子,受用欲乐,但遵行他的教导,回应他的劝告,已超越疑惑,远离困惑,获得无畏,于导师的教法中,不再依赖他人?”
“不只一百……或五百,而是有更多更多的女居士,我的弟子们,身着白衣,受用欲乐,但遵行我的教导,回应我的劝告,已超越疑惑,远离困惑,获得无畏,于导师的教法中,不再依赖他人。”
13. “乔达摩 (Gotama) 大师,如果只有乔达摩大师于此法中有所成就,而没有比丘成就,那么此梵行于此方面则为不圆满;但因为乔达摩大师和诸比丘皆于此法中有所成就,故此梵行于此方面是圆满的。如果只有乔达摩大师和诸比丘于此法中有所成就,而没有比丘尼成就,那么此梵行于此方面则为不圆满;但因为乔达摩大师、诸比丘与比丘尼皆于此法中有所成就,故此梵行于此方面是圆满的。如果只有乔达摩大师、诸比丘与比丘尼于此法中有所成就,而没有过着梵行生活的白衣男居士成就,那么此梵行于此方面则为不圆满;但因为乔达摩大师、诸比丘与比丘尼,以及过着梵行生活的白衣男居士皆于此法中有所成就,故此梵行于此方面是圆满的。如果只有乔达摩大师、诸比丘与比丘尼,以及过着梵行生活的白衣男居士于此法中有所成就,而没有受用欲乐的白衣男居士成就,那么此梵行于此方面则为不圆满;但因为乔达摩大师、诸比丘与比丘尼,以及不论是过着梵行生活或受用欲乐的白衣男居士皆于此法中有所成就,故此梵行于此方面是圆满的。如果只有乔达摩大师、诸比丘与比丘尼,以及白衣男居士……于此法中有所成就,而没有过着梵行生活的白衣女居士成就,那么此梵行于此方面则为不圆满;但因为乔达摩大师、诸比丘与比丘尼、白衣男居士……以及过着梵行生活的白衣女居士皆于此法中有所成就,故此梵行于此方面是圆满的。如果只有乔达摩大师、诸比丘与比丘尼、白衣男居士……以及过着梵行生活的白衣女居士于此法中有所成就,而没有受用欲乐的白衣女居士成就,那么此梵行于此方面则为不圆满;但因为乔达摩大师、诸比丘与比丘尼,以及不论是过着梵行生活或受用欲乐的白衣男居士,和不论是过着梵行生活或受用欲乐的白衣女居士,皆于此法中有所成就,故此梵行于此方面是圆满的。
14. “犹如恒河,倾向于海,朝向于海,奔流于海,最终入海。同样地,乔达摩 (Gotama) 大师的僧团,包含出家众与在家众,皆倾向于涅槃,朝向于涅槃,奔流于涅槃,最终证得涅槃。”
(出自 MN 73: Mahavacchagotta Sutta; I 490–93)
(5)七种圣者
11. “诸比丘,我并非对所有比丘都说他们尚须以不放逸精勤;我也并非对所有比丘都说他们无须再以不放逸精勤。
12. “对于那些已断尽诸漏的阿罗汉比丘,他们已圆满梵行,所作已办,已卸重担,已达己利,已彻底断除有结,以究竟智而完全解脱,我不说他们尚须以不放逸精勤。为何如此?因为他们已以不放逸完成其修行;他们已不可能再放逸。
13. “对于那些仍是学人、心尚未达目标、仍在追求无上安稳离缚的比丘,我说他们尚须以不放逸精勤。为何如此?因为当那些尊者使用合适的住处、亲近善友并培育其根力时,他们可以于此生中,以亲身智证,证入并安住于梵行的至高目标,那正是善男子为之而出家、过无家生活的目的。见到不放逸能为这些比丘带来此等成果,故我说他们尚须以不放逸精勤。
14. “诸比丘,世间现有七种人。是哪七种?他们是:俱解脱者、慧解脱者、身证者、见至者、信解脱者、随法行者、以及随信行者。
15. “何谓俱解脱者?于此,有人以身触证并安住于那些超越色界的、寂静的、无色的解脱,并以智慧亲见而断尽诸漏。这类人称为俱解脱者。13 我不说这样的比丘尚须以不放逸精勤。为何如此?他已以不放逸完成其修行;他已不可能再放逸。
16. “何谓慧解脱者?于此,有人未以身触证并安住于那些超越色界的、寂静的、无色的解脱,但以智慧亲见而断尽诸漏。这类人称为慧解脱者。14 我不说这样的比丘尚须以不放逸精勤。为何如此?他已以不放逸完成其修行;他已不可能再放逸。
17. “何谓身证者?于此,有人以身触证并安住于那些超越色界的、寂静的、无色的解脱,并以智慧亲见而断尽部分诸漏。这类人称为身证者。15 我说这样的比丘尚须以不放逸精勤。为何如此?因为当那位尊者使用合适的住处、亲近善友并培育其根力时,他可以于此生中,以亲身智证,证入并安住于梵行的至高目标,那正是善男子为之而出家、过无家生活的目的。见到不放逸能为此等比丘带来此等成果,故我说他尚须以不放逸精勤。
18. “何谓见至者?于此,有人未以身触证并安住于那些超越色界的、寂静的、无色的解脱,但以智慧亲见而断尽部分诸漏,并且他已以智慧审察并检验如来所宣说的教法。这类人称为见至者。16 我说这样的比丘尚须以不放逸精勤。为何如此?因为当那位尊者……过无家生活的目的。见到不放逸能为此等比丘带来此等成果,故我说他尚须以不放逸精勤。
19. “何谓信解脱者?于此,有人未以身触证并安住于那些超越色界的、寂静的、无色的解脱,但以智慧亲见而断尽部分诸漏,且他对如来的信心已确立、生根、稳固。这类人称为信解脱者。17 我说这样的比丘尚须以不放逸精勤。为何如此?因为当那位尊者……过无家生活的目的。见到不放逸能为此等比丘带来此等成果,故我说他尚须以不放逸精勤。
20. “何谓随法行者?于此,有人未以身触证并安住于那些超越色界的、寂静的、无色的解脱,其诸漏亦未以智慧亲见而断尽,但那些如来所宣说的教法,经他以智慧作充分思惟后,已能接受。此外,他具足这些特质: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以及慧根。这类人称为随法行者。18 我说这样的比丘尚须以不放逸精勤。为何如此?因为当那位尊者……过无家生活的目的。见到不放逸能为此等比丘带来此等成果,故我说他尚须以不放逸精勤。
21. “何谓随信行者?于此,有人未以身触证并安住于那些超越色界的、寂静的、无色的解脱,其诸漏亦未以智慧亲见而断尽,然而他对如来有足够的信心与爱敬。此外,他具足这些特质: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以及慧根。这类人称为随信行者。我说这样的比丘尚须以不放逸精勤。为何如此?因为当那位尊者使用合适的住处、亲近善友并培育其根力时,他可以于此生中,以亲身智证,证入并安住于梵行的至高目标,那正是善男子为之而出家、过无家生活的目的。见到不放逸能为此等比丘带来此等成果,故我说他尚须以不放逸精勤。”
(出自 MN 70: Kitagiri Sutta; I 477–79)
第二篇:入流
(1)导向入流的四项助缘
世尊对尊者舍利弗 (Sāriputta) 说:“舍利弗 (Sāriputta),人们常说:‘入流的助缘,入流的助缘。’那么,舍利弗 (Sāriputta),什么是入流的助缘呢?”
“尊者,亲近善人,是入流的助缘。听闻正法,是入流的助缘。如理作意,是入流的助缘。法随法行,是入流的助缘。”
“善哉,善哉,舍利弗 (Sāriputta)!如你所说。舍利弗 (Sāriputta),人们常说:‘流,流。’那么,什么是流呢?”
“尊者,此八正道即是流;也就是: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善哉,善哉,舍利弗 (Sāriputta)!如你所说。舍利弗 (Sāriputta),人们常说:‘须陀洹,须陀洹。’那么,什么是须陀洹呢?”
“尊者,拥有此八正道的人,被称为须陀洹:即某名某姓的这位尊者。”
“善哉,善哉,舍利弗 (Sāriputta)!拥有此八正道的人是须陀洹:即某名某姓的这位尊者。”
(SN 55:5; V 410–11)
(2)进入正性决定
“诸比丘,眼是无常的、变易的、会转变的。耳……鼻……舌……身……意是无常的、变易的、会转变的。对这些教法怀有信心并如此决意者,称为随信行者,已进入正性决定,19进入善人之地,超越凡夫之地。他不可能造作任何会使他重生于地狱、畜生道或饿鬼界的业;他不可能在未证悟须陀洹果之前命终。20
“若人以智慧充分思惟后,接受这些教法,则称为随法行者,已进入正性决定,进入善人之地,超越凡夫之地。他不可能造作任何会使他重生于地狱、畜生道或饿鬼界的业;他不可能在未证悟须陀洹果之前命终。
“若人如此了知并亲见这些教法,则称为须陀洹,不再受缚于下界,命运已定,以觉悟为归宿。”21
(SN 25:1; III 225)
(3)法的突破
世尊以指甲沾取少许泥土,然后对诸比丘说:
“诸比丘,你们认为如何,何者为多:我指甲上沾的这一点点泥土,还是这整个大地?”
“尊者,大地更多。世尊指甲上沾的这一点点泥土微不足道。它不及大地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
“同样地,诸比丘,对于一位已见法、已实现突破的圣弟子而言,已被摧毁与灭尽的苦更多,而剩余的苦则微不足道。后者不及前者已被摧毁与灭尽的苦蕴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因为最多只剩下七次生命。诸比丘,实现法的突破有如此大的利益,获得法眼有如此大的利益。”22
(SN 13:1; II 133–34)
(4)须陀洹的四项要素
“诸比丘,一位具足四法的圣弟子是须陀洹,不再受缚于下界,命运已定,以觉悟为归宿。
“是哪四法?于此,诸比丘,一位圣弟子对佛陀具足确证的净信23,即:‘世尊是阿罗汉、圆满觉悟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他对法具足确证的净信,即:‘法乃世尊所善说,是直接可见的、即时的、欢迎来看的、值得应用的、智者可亲身体证的。’他对僧团具足确证的净信,即:‘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善行道者,是正直行道者,是如理行道者,是正当行道者;也就是四双八辈——此世尊的弟子僧团应受供养、应受款待、应受布施、应受合掌致敬,是世间无上的福田。’他拥有圣者所珍视的戒德,不破、不穿、无斑、无点、能导向解脱、为智者所赞叹、不为执取、能导向定。
“诸比丘,一位拥有这四法的圣弟子是须陀洹,不再受缚于下界,命运已定,以觉悟为归宿。”
(SN 55:2; V 343–44)
(5)胜于大地主权
“诸比丘,即使一位转轮圣王,于四大洲行使至高无上的主权,身坏命终后,往生于善趣、天界,与三十三天(Tāvatimsa)的天人为伴,在难陀那园(Nandana Grove)中,有天女众围绕,受用并具足天界五欲之乐,然而,由于他不具备四法,他仍未解脱于地狱、畜生道及饿鬼界,未解脱于苦界、恶趣、下界。24 诸比丘,即使一位圣弟子以乞食维生、身穿粪扫衣,然而,由于他具足四法,他已解脱于地狱、畜生道及饿鬼界,解脱于苦界、恶趣、下界。是哪四法呢?对佛、法、僧的确证净信,以及圣者所珍视的戒德。诸比丘,获得四大洲的主权与获得此四法相比,获得四大洲的主权,其价值不及获得此四法的十六分之一。”
(SN 55:1; V 342)
第三篇:不还
(1)断除五下分结
7. “阿难 (Ānanda),有一条导向断除五下分结的道路与方法。任何人若不依此道、此法,而想了知、亲见或断除五下分结——这是不可能的。譬如有一棵具足心材的伟岸大树,任何人若不先砍穿其树皮与边材,就想取出其心材,这是不可能的。同样地,对于断除五下分结也是如此。
“阿难 (Ānanda),有一条导向断除五下分结的道路与方法。有人依此道、此法,而能了知、亲见并断除五下分结——这是可能的。譬如有一棵具足心材的伟岸大树,有人先砍穿其树皮与边材,便能取出其心材。同样地,对于断除五下分结也是如此。
8. “阿难 (Ānanda),譬如恒河水满及岸,乌鸦可于岸边饮水,此时来了一个孱弱之人,心想:‘我要用双臂游过这恒河,安全到达对岸’;然而他将无法安全渡过。同样地,当为某人说法以断除身见时,若其心不趣入、不获得信心、稳固与决意,则他可被视为如同那孱弱之人。25
“阿难 (Ānanda),譬如恒河水满及岸,乌鸦可于岸边饮水,此时来了一个强壮之人,心想:‘我要用双臂游过这恒河,安全到达对岸’;而他将能够安全渡过。同样地,当为某人说法以断除身见时,若其心趣入、并获得信心、稳固与决意,则他可被视为如同那强壮之人。”
9. “阿难,什么是断除五下分结的道路与方法呢?于此,通过远离诸资具,26通过断除诸不善法,通过彻底平息身行,远离诸欲乐,远离诸不善法,一位比丘进入并安住于初禅,此禅伴随着寻与伺,由远离而生喜与乐。”
“于其中存在的任何色、受、想、行、识,他视此诸法为无常、为苦、为病、为痈、为箭、为灾、为难、为异、为坏、为空、为无我。27他将心从这些法中转离,并将其导向不死界,心想:‘此是寂静,此是殊胜,即一切行之止息,一切资具之舍离,爱尽,离欲,灭,涅槃。’28若他于此安住,即能证得诸漏灭尽。但若他未能证得诸漏灭尽,那么,正是通过那法欲、法喜,随着五下分结的断尽,他成为化生者[于净居天],在那里证得最终的涅槃,永不从此世间返回。29这便是断除五下分结的道路与方法。”
10–12. “再者,随着寻与伺的平息,一位比丘进入并安住于第二禅……再者,随着喜的消退,一位比丘……进入并安住于第三禅……再者,随着舍离乐与苦……一位比丘进入并安住于第四禅,此禅不苦不乐,由舍而念清净。”
“于其中存在的任何色、受、想、行、识,他视此诸法为无常……为无我。他将心从这些法中转离,并将其导向不死界……这便是断除五下分结的道路与方法。”
13. “再者,通过完全超越色想,随着有对想的消失,不作意种种想,觉知到‘空间是无限的’,一位比丘进入并安住于空无边处。”
“于其中存在的任何受、想、行、识,30他视此诸法为无常……为无我。他将心从这些法中转离,并将其导向不死界……这便是断除五下分结的道路与方法。”
14. “再者,通过完全超越空无边处,觉知到‘识是无限的’,一位比丘进入并安住于识无边处。”
“于其中存在的任何受、想、行、识,他视此诸法为无常……为无我。他将心从这些法中转离,并将其导向不死界……这便是断除五下分结的道路与方法。”
15. “再者,通过完全超越识无边处,觉知到‘一无所有’,一位比丘进入并安住于无所有处。”
“于其中存在的任何受、想、行、识,他视此诸法为无常、为苦、为病、为痈、为箭、为灾、为难、为异、为坏、为空、为无我。他将心从这些法中转离,并将其导向不死界,心想:‘此是寂静,此是殊胜,即一切行之止息,一切资具之舍离,爱尽,离欲,灭,涅槃。’若他于此安住,即能证得诸漏灭尽。但若他未能证得诸漏灭尽,那么,正是通过那法欲、法喜,随着五下分结的断尽,他成为化生者[于净居天],在那里证得最终的涅槃,永不从此世间返回。这便是断除五下分结的道路与方法。”
(出自《中部·六十四·摩罗迦大经》;I 434–37)
(2)四种人
“诸比丘,世间存在着四种人。是哪四种?”
“在此,诸比丘,有人于此生中,通过有行而证得涅槃。在此,有人身坏命终后,通过有行而证得最终的涅槃。在此,有人于此生中,通过无行而证得最终的涅槃。在此,有人身坏命终后,通过无行而证得最终的涅槃。”
“诸比丘,人如何于此生中,通过有行而证得涅槃呢?于此,一位比丘安住于观身不净,感知食物的厌恶,感知对整个世间的不乐,观一切行为无常;并且,死想于其内善安立。31他安住并依止于此学人的五力:信力、惭力、愧力、精进力与慧力。此五根于他极为强劲: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与慧根。因这五根的强劲,他于此生中,通过有行而证得涅槃。这便是人如何于此生中,通过有行而证得涅槃。”
“诸比丘,人如何身坏命终后,通过有行而证得涅槃呢?于此,一位比丘安住于观身不净……并且,死想于其内善安立。他安住并依止于此学人的五力:信力……与慧力。此五根于他相对微弱:信根……与慧根。因这五根的微弱,他身坏命终后,通过有行而证得涅槃。这便是人如何身坏命终后,通过有行而证得涅槃。”
“诸比丘,人如何于此生中,通过无行而证得涅槃呢?于此,远离诸欲乐,远离诸不善法,一位比丘进入并安住于初禅……第四禅。他安住并依止于此学人的五力:信力……与慧力。此五根于他极为强劲:信根……与慧根。因这五根的强劲,他于此生中,通过无行而证得涅槃。这便是人如何于此生中,通过无行而证得涅槃。”
“诸比丘,人如何身坏命终后,通过无行而证得涅槃呢?于此,远离诸欲乐,远离诸不善法,一位比丘进入并安住于初禅……第四禅。他安住并依止于此学人的五力:信力……与慧力。此五根于他相对微弱:信根……与慧根。因这五根的微弱,他身坏命终后,通过无行而证得涅槃。这便是人如何身坏命终后,通过无行而证得涅槃。”
“诸比丘,这便是世间存在的四种人。”
(《增支部·四集·一六九》;II 155–56)
(3)六种顺明分法
一时,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林精舍,松鼠喂食处。当时,居士迪伽伍(Dīghāvu)生病了,受苦,病重。于是居士迪伽伍(Dīghāvu)对他的父亲,长者乔帝卡(Jotika)说:“来,长者,请去见世尊,以我的名义顶礼他的双足,并说:‘尊者,居士迪伽伍(Dīghāvu)生病了,受苦,病重;他顶礼世尊的双足。’然后说:‘尊者,若世尊能出于慈悲,来到居士迪伽伍(Dīghāvu)的住所,那就太好了。’”
“好的,亲爱的。”长者乔帝卡(Jotika)答道,他走近世尊,向他行礼,坐在一旁,并传达了信息。世尊默然应允。
然后世尊穿好衣服,持衣钵,前往居士迪伽伍(Dīghāvu)的住所。他在准备好的座位上坐下,对居士迪伽伍(Dīghāvu)说:“迪伽伍(Dīghāvu),希望你还能忍受,希望你病情好转。希望你的苦受正在减退而不是增加,并且可以察觉到它们在减退,而不是增加。”
“尊者,我无法忍受,病情没有好转。我身上剧烈的苦受正在增加,而不是减退,可以察觉到它们在增加,而不是减退。”
“因此,迪伽伍(Dīghāvu),你应该这样训练自己:‘我将成为一位对佛、法、僧有确信的人,并且持守圣者所喜爱的戒行,此戒不破、不穿、无瑕、无疵、能导向解脱、为智者所称赞、不为渴爱所执取、能导向禅定。’你应该这样训练自己。”
“尊者,关于世尊所教导的这四种入流支,这些法存在于我身中,我亦随顺这些法而住。因为,尊者,我对佛、法、僧有确信,并且我持守圣者所喜爱的戒行。”
“因此,迪伽伍(Dīghāvu),安住于这四种入流支,你应该进一步培育六种顺明分法。于此,迪伽伍(Dīghāvu),安住于观一切行为无常,感知无常中的苦,感知苦中的无我,感知舍离,感知离欲,感知灭尽。32你应该这样训练自己。”
“尊者,关于世尊所教导的这六种顺明分法,这些法存在于我身中,我亦随顺这些法而住。因为,尊者,我安住于观一切行为无常,感知无常中的苦,感知苦中的无我,感知舍离,感知离欲,感知灭尽。然而,尊者,我希望我去世后,我的父亲不会感到悲伤。”
“不要担心这个,亲爱的迪伽伍(Dīghāvu)。来,亲爱的迪伽伍(Dīghāvu),仔细听世尊对你说的话。”
然后,世尊对居士迪伽伍(Dīghāvu)作此教诫后,从座位上起身离开。世尊离开后不久,居士迪伽伍(Dīghāvu)就去世了。
之后,一些比丘来到世尊面前,向他行礼,坐在一旁说:“尊者,居士迪伽伍(Dīghāvu)已经去世了。他的去处是哪里?他重生在何处?”
“诸比丘,居士迪伽伍(Dīghāvu)是位智者。他依法修行,未曾因法而烦扰我。随着五下分结的彻底断尽,居士迪伽伍(Dīghāvu)已成为化生者[于净居天],将在那里证得涅槃,不再从此世间返回。”
(《相应部·五五·三》;V 344–46)
(4)五种不还者
“诸比丘,当这七觉支被如此培育和修习时,可预期有七种果与利益。是哪七种果与利益?”
“其一,于此生中尽早证得究竟智(阿罗汉果)。”
“若未能于此生中尽早证得究竟智,则于临终时证得究竟智。”
“若未能于此生中尽早证得究竟智,亦未能于临终时证得,则随着五下分结的彻底断尽,证得中般涅槃。33”
“若未能于此生中尽早证得究竟智……或证得中般涅槃,则随着五下分结的彻底断尽,证得生般涅槃。”
“若未能于此生中尽早证得究竟智……或证得生般涅槃,则随着五下分结的彻底断尽,证得无行般涅槃。”
“若未能于此生中尽早证得究竟智……或证得无行般涅槃,则随着五下分结的彻底断尽,证得有行般涅槃。”
“若未能于此生中尽早证得究竟智……或证得有行般涅槃,则随着五下分结的彻底断尽,成为上流至色究竟天者。”
“诸比丘,当七觉支被如此培育和修习时,可预期有这七种果与利益。”
(《相应部·四六·三》;V 69–70)
第四篇:阿罗汉
(1)去除“我是”的残余我慢
有一次,一些长老比丘住在拘舍弥(Kosambī)的瞿师罗园(Ghosita’s Park)。当时,尊者差摩迦(Khemaka)住在枣树园,生病了,受苦,病重。
傍晚时分,那些长老比丘从独处中出来,对尊者陀索迦(Dāsaka)说:“来,陀索迦(Dāsaka)道友,去见差摩迦(Khemaka)比丘,对他说:‘差摩迦(Khemaka)道友,诸位长老问候您:我们希望您还能忍受,道友,希望您病情好转。希望您的苦受正在减退而不是增加,并且可以察觉到它们在减退,而不是增加。’”
“好的,道友们。”尊者陀索迦(Dāsaka)答道,他走近尊者差摩迦(Khemaka)并传达了信息。
[尊者差摩迦(Khemaka)答道:]“道友,我无法忍受,病情没有好转。我身上剧烈的苦受正在增加,而不是减退,可以察觉到它们在增加,而不是减退。”
然后尊者陀索迦(Dāsaka)回到长老比丘们那里,报告了尊者差摩迦(Khemaka)所说的话。他们对他说:“来,陀索迦(Dāsaka)道友,去见差摩迦(Khemaka)比丘,对他说:‘差摩迦(Khemaka)道友,诸位长老问候您:世尊曾说有这五取蕴;即是:色、受、想、行、识。尊者差摩迦(Khemaka)是否视这五取蕴中的任何一法为我或我所?’”
“好的,道友们。”尊者陀索迦(Dāsaka)答道,他走近尊者差摩迦(Khemaka)并传达了信息。
[尊者差摩迦(Khemaka)答道:]“世尊曾说有这五取蕴;即是:色、受、想、行、识。于此五取蕴中,我不视任何一法为我或我所。”
然后尊者陀索迦(Dāsaka)回到长老比丘们那里,报告了尊者差摩迦(Khemaka)所说的话。他们答道:“来,陀索迦(Dāsaka)道友,去见差摩迦(Khemaka)比丘,对他说:‘若尊者差摩迦(Khemaka)不视这五蕴中的任何一法为我或我所,那么他就是一位阿罗汉,一位诸漏已尽者。’”34
“好的,道友们。”尊者陀索迦(Dāsaka)答道,他走近尊者差摩迦(Khemaka)并传达了信息。
[尊者差摩迦(Khemaka)答道:]“世尊曾说有这五取蕴;即是:色、受、想、行、识。我虽不视这五取蕴中的任何一法为我或我所,但我并非阿罗汉,并非诸漏已尽者。道友们,对于这五取蕴,‘我是’[之念]于我尚未消失,但我并不认为[其中任何一法]是‘这个是我’。”35
然后尊者陀索迦(Dāsaka)回到长老比丘们那里,报告了尊者差摩迦(Khemaka)所说的话。他们答道:“来,陀索迦(Dāsaka)道友,去见差摩迦(Khemaka)比丘,对他说:‘诸位长老问候您,差摩迦(Khemaka)道友:差摩迦(Khemaka)道友,当您说这个“我是”时——您说的是什么为“我是”?您是说色为“我是”,还是说“我是”离于色?您是说受……想……行……识为“我是”,还是说“我是”离于识?当您说这个“我是”时,差摩迦(Khemaka)道友,您说的是什么为“我是”?’”
“好的,道友们。”尊者陀索迦(Dāsaka)答道,他走近尊者差摩迦(Khemaka)并传达了信息。
“够了,陀索迦(Dāsaka)道友!何必来回奔波?道友,把我的手杖拿来。我自己去见长老比丘们。”
然后,尊者差摩迦(Khemaka)拄着手杖,来到长老比丘们面前,与他们互致问候,然后坐在一旁。长老比丘们对他说:“差摩迦(Khemaka)道友,当您说这个‘我是’时……您说的是什么为‘我是’?”
“道友们,我不说色为‘我是’,也不说‘我是’离于色。我不说受为‘我是’……不说想为‘我是’……不说行为‘我是’……不说识为‘我是’,也不说‘我是’离于识。道友们,虽然对于这五取蕴,‘我是’[之念]于我尚未消失,但我并不认为[其中任何一法]是‘这个是我’。”
“道友们,譬如有一朵青莲、红莲或白莲的香气。如果有人说‘香气属于花瓣’,或‘香气属于花茎’,或‘香气属于花蕊’,这样说正确吗?”
“不正确,道友。”
“那么,道友们,要如何回答才算正确呢?”
“正确地回答,道友,应该回答说:‘香气属于花朵。’”
“同样地,道友们,我不说色为‘我是’,也不说‘我是’离于色。我不说受为‘我是’……不说想为‘我是’……不说行为‘我是’……不说识为‘我是’,也不说‘我是’离于识。道友们,虽然对于这五取蕴,‘我是’[之念]于我尚未消失,但我并不认为[其中任何一法]是‘这个是我’。”
“道友们,即使一位圣弟子已断除五下分结,然而,对于五取蕴,他仍然残留着一种‘我是’的我慢,一种‘我是’的欲求,一种‘我是’的随眠烦恼,尚未被根除。此后某个时候,他安住于观五取蕴的生灭:‘色是如此,其生起是如此,其息灭是如此;受是如此……想是如此……行是如此……识是如此,其生起是如此,其息灭是如此。’当他如此安住于观五取蕴的生灭时,那尚未被根除的‘我是’的残余我慢,‘我是’的欲求,‘我是’的随眠烦恼——便得以根除。”
“道友们,譬如一块布变脏了,沾上了污渍,主人把它交给洗衣工。洗衣工会用清洁盐、碱液或牛粪均匀地擦洗它,然后在清水中漂洗。即使那块布变得纯净清洁,它仍会残留着尚未消失的清洁盐、碱液或牛粪的气味。然后洗衣工会把它还给主人。主人会把它放进一个香气馥郁的箱子里,那尚未消失的清洁盐、碱液或牛粪的残余气味就会消失。36”
“同样地,道友们,即使一位圣弟子已断除五下分结,然而,对于五取蕴,他仍然残留着一种‘我是’的我慢,一种‘我是’的欲求,一种‘我是’的随眠烦恼,尚未被根除……当他如此安住于观五取蕴的生灭时,那尚未被根除的‘我是’的残余我慢,‘我是’的欲求,‘我是’的随眠烦恼——便得以根除。”
此话说完,长老比丘们对尊者差摩迦(Khemaka)说:“我们提问并非为了困扰尊者差摩迦(Khemaka),但我们认为尊者差摩迦(Khemaka)有能力详细地解释、教导、宣说、确立、揭示、分析和阐明世尊的教法。而尊者差摩迦(Khemaka)已经详细地解释、教导、宣说、确立、揭示、分析和阐明了世尊的教法。”
于是,长老比丘们对尊者差摩迦(Khemaka)的言论感到欢欣和喜悦。就在这段开示进行中,六十位长老比丘和尊者差摩迦(Khemaka)的心,因无执取而从诸漏中解脱。
(《相应部·二二·八九》;III 126–32)
(2)学人与阿罗汉
在拘舍弥(Kosambī)的瞿师罗园(Ghosita’s Park),世尊对诸比丘说:
“诸比丘,有一种方法,通过它,一位身为学人、立于学人位的比丘,可以了知:‘我是一位学人’;而一位超越学人、立于无学位的比丘,可以了知:‘我是一位无学人’。”
“诸比丘,通过什么方法,一位身为学人、立于学人位的比丘,能了知:‘我是一位学人’呢?”
“于此,诸比丘,一位身为学人的比丘如实了知:‘这是苦。这是苦的起源。这是苦的止息。这是导向苦止息的道路。’这便是身为学人、立于学人位的比丘了知‘我是一位学人’的方法。”
“再者,诸比丘,一位身为学人的比丘这样思惟:‘在此之外,37是否有其他沙门或婆罗门,能教导像世尊那样真实、真确、实在的法?’他如此了知:‘在此之外,没有其他沙门或婆罗门,能教导像世尊那样真实、真确、实在的法。’这也是身为学人、立于学人位的比丘了知‘我是一位学人’的方法。”
“再者,诸比丘,一位身为学人的比丘了知五根——信根、精进根、念根、定根、慧根。他尚未以身触证它们的终点、顶点、果实和最终目标;但已用智慧洞察并见到。38这也是身为学人、立于学人位的比丘了知‘我是一位学人’的方法。”
“诸比丘,通过什么方法,一位超越学人、立于无学位的比丘,能了知:‘我是一位无学人’呢?于此,诸比丘,一位超越学人的比丘了知五根——信根……慧根。他以身触证它们的终点、顶点、果实和最终目标而安住;并已用智慧洞察并见到。这便是超越学人、立于无学位的比丘了知‘我是一位无学人’的方法。”
“再者,诸比丘,一位超越学人的比丘了知六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他了知:‘这六根将完全、彻底地无余止息,并且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都不会再有其他六根生起。’这也是超越学人、立于无学位的比丘了知‘我是一位无学人’的方法。”
(《相应部·四八·五三》;V 229–30)
(3)一位门闩已举的比丘
30. “诸比丘,阿罗汉被称为门闩已举者,沟堑已填者,柱石已拔者,无门栓者,降下旗帜的圣者,放下重担者,无缚者。”
31. “阿罗汉如何是门闩已举者?于此,阿罗汉已舍弃无明,从根斩断,使之如棕榈树桩,将其废除,使其不再有未来之生。他如此成为门闩已举者。”
32. “阿罗汉如何是沟堑已填者?于此,阿罗汉已舍弃轮回再生,更新存在的进程,从根斩断……使其不再有未来之生。他如此成为沟堑已填者。”
33. “阿罗汉如何是柱石已拔者?于此,阿罗汉已舍弃渴爱,从根斩断……使其不再有未来之生。他如此成为柱石已拔者。”
34. “阿罗汉如何是无门栓者?于此,比丘已舍弃五下分结,从根斩断……使其不再有未来之生。他如此成为无门栓者。”
35. “阿罗汉如何是降下旗帜、放下重担、无缚的圣者?于此,阿罗汉已舍弃‘我是’的我慢,从根斩断……使其不再有未来之生。他如此成为降下旗帜、放下重担、无缚的圣者。”
(出自《中部·二二·蛇喻经》;I 139–40)
(4)阿罗汉不能做的九件事
“过去及现在,我都宣说,一位诸漏已尽的阿罗汉比丘——已圆满梵行,所作已办,已放下重担,已达己利,已彻底断除有结,以究竟智而解脱者——于九事上不可能违越:他不可能杀生,不可能不与取,不可能行淫,不可能故意说谎,不可能像过去作居士时那样积蓄受用;此外,他不可能因欲而行错误之道,不可能因嗔而行错误之道,不可能因痴而行错误之道,不可能因畏而行错误之道。过去及现在,我都宣说,一位阿罗汉比丘于此九事上不可能违越。”
(出自《增支部·九集·七》;IV 370–71)
(5)不动摇之心
[尊者舍利弗(Sāriputta)说:]“道友,当一位比丘的心如此解脱时,即使强大的、眼所识知的色境进入他的视野范围,它们也不会占据他的心;他的心保持无染、稳固,达到不动,而他观察它们的息灭。即使强大的、耳所识知的声音……鼻所识知的气味……舌所识知的味道……身所识知的触……意所识知的法进入他的意识范围,它们也不会占据他的心;他的心保持无染、稳固,达到不动,而他观察它们的息灭。道友,譬如有一根十六米长的石柱,八米埋入地下,八米露出地面。这时,一场强烈的暴风雨从东方袭来:那石柱不会摇动,不会晃动,不会颤动。然后一场强烈的暴风雨从北方……从西方……从南方袭来:那石柱不会摇动,不会晃动,不会颤动。为何如此?因为基座深,且石柱深植。同样地,对于一位心如此解脱的比丘,若强大的感官对象进入其范围,它们也不会占据他的心;他的心保持无染、稳固,达到不动,而他观察它们的息灭。”
(出自《增支部·九集·二六》;IV 404–5)
(6)阿罗汉比丘的十力
佛陀问尊者舍利弗(Sāriputta):“舍利弗(Sāriputta),一位阿罗汉比丘拥有多少力,凭借这些力,他宣称自己已证得诸漏灭尽?”
“尊者,阿罗汉比丘有十力,凭借这些力,他宣称自己已证得诸漏灭尽。是哪十力?”
“于此,尊者,对于一位阿罗汉比丘,一切行已被以正慧如实善见为无常。这是一位阿罗汉比丘之力,他以此力为基础,宣称自己已证得诸漏灭尽。”
“再者,尊者,对于一位阿罗汉比丘,诸欲乐已被以正慧如实善见为如同炭火坑。这也是一位阿罗汉比丘之力……”
“再者,尊者,阿罗汉比丘的心倾向、趋向、趣向于独处;它安住于独处,乐于出离,并完全断除了所有作为诸漏之基的事物。这也是一位阿罗汉比丘之力……”
“再者,尊者,对于一位阿罗汉比丘,四念住已被培育至善于培育的程度。这也是一位阿罗汉比丘之力……”
“再者,尊者,对于一位阿罗汉比丘,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已被培育至善于培育的程度。尊者,这也是阿罗汉比丘的一种力量,他依此宣称自己已证得诸漏已尽。”39
(AN 10:90; V 174–75)
(7)寂静的贤者
20. [佛陀进一步对弗古沙提(Pukkusāti)说:] “然后[在思惟六界之后],只剩下舍,清净而明亮,柔软、堪任且光耀。40……
21. “他如此了知:‘如果我将这如此清净而明亮的舍导向空无边处,并依此培育我的心,那么我的这个舍,以此处为助缘,执着于它,将会长久地持续。41 如果我将这如此清净而明亮的舍导向识无边处……导向无所有处……导向非想非非想处,并依此培育我的心,那么我的这个舍,以此处为助缘,执着于它,将会长久地持续。’
22. “他如此了知:‘如果我将这如此清净而明亮的舍导向空无边处,并依此培育我的心,这将是因缘和合的。42 如果我将这如此清净而明亮的舍导向识无边处……导向无所有处……导向非想非非想处,并依此培育我的心,这将是因缘和合的。’ 他不构造或生起任何趋向于“有”或“无有”的意愿。43 由于他不构造或生起任何趋向于“有”或“无有”的意愿,他便不执取这世间的任何事物。不执取,他便不被搅动。不被搅动,他便亲身证得 Nibbāna。他了知:‘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44
23. “如果他感受到一种乐受,45他了知:‘它是无常的;其中无可执持;其中无可喜乐。’ 如果他感受到一种苦受,他了知:‘它是无常的;其中无可执持;其中无可喜乐。’ 如果他感受到一种不苦不乐受,他了知:‘它是无常的;其中无可执持;其中无可喜乐。’
24. “如果他感受到一种乐受,他是离执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到一种苦受,他是离执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到一种不苦不乐受,他是离执地感受它。当他感受到一种身尽的感受时,他了知:‘我感受到一种身尽的感受。’ 当他感受到一种命尽的感受时,他了知:‘我感受到一种命尽的感受。’ 他了知:‘身体瓦解,生命终结之时,所有被感受到的,因不被喜乐,于此都将变得清凉。’46 比丘,就像一盏油灯依赖油和灯芯而燃烧,当油和灯芯耗尽时,如果得不到更多的燃料,它便因缺乏燃料而熄灭;同样地,当他感受到一种身尽的感受……一种命尽的感受时,他了知:‘我感受到一种命尽的感受。’ 他了知:‘身体瓦解,生命终结之时,所有被感受到的,因不被喜乐,于此都将变得清凉。’47
25. “因此,具备[此智慧]的比丘,便具备了智慧的至上根基。因为,比丘,这便是至上的圣慧,即了知一切苦的寂灭。
26. “他的解脱,建立在真理之上,是不可动摇的。因为,比丘,凡有欺罔性质的,即是虚假的;凡有不欺罔性质的——Nibbāna,即是真实的。因此,具备[此真理]的比丘,便具备了真理的至上根基。因为,比丘,这便是至上的圣谛,即具有不欺罔性质的 Nibbāna。48
27. “从前,当他无明时,他承揽和接受各种获取;49如今他已舍弃它们,从根斩断,使之如断头棕榈树,彻底根除,不再于未来生起。因此,具备[此舍离]的比丘,便具备了舍离的至上根基。因为,比丘,这便是至上的圣舍离,即舍离一切获取。
28. “从前,当他无明时,他经历贪婪、欲望和贪爱;如今他已舍弃它们,从根斩断,使之如断头棕榈树,彻底根除,不再于未来生起。从前,当他无明时,他经历愤怒、恶意和憎恨;如今他已舍弃它们,从根斩断,使之如断头棕榈树,彻底根除,不再于未来生起。从前,当他无明时,他经历无明和愚痴;如今他已舍弃它们,从根斩断,使之如断头棕榈树,彻底根除,不再于未来生起。因此,具备[此寂静]的比丘,便具备了寂静的至上根基。因为,比丘,这便是至上的圣寂静,即贪、嗔、痴的平息。
29. “所以,正是在此意义上说:‘不应轻忽智慧,应守护真理,应培育舍离,应为寂静而修学。’
30. “‘构想的浪潮,无法席卷安住于此[根基]者,当构想的浪潮不再席卷他时,他便被称为寂静的贤者。’50 如是说。这是就什么而说的呢?
31. “比丘,‘我是’是一种构想;‘我是这个’是一种构想;‘我将是’是一种构想;‘我将不是’是一种构想;‘我将有色身’是一种构想;‘我将是无色身’是一种构想;‘我将有想’是一种构想;‘我将无想’是一种构想;‘我将非想非非想’是一种构想。51 构想是一种病,构想是一个肿瘤,构想是一支箭。比丘,通过克服所有的构想,一个人被称为寂静的贤者。而寂静的贤者不生、不老、不死;他不被动摇,也不渴求。因为在他之内,没有任何使他可能出生的东西。52 不生,他如何会老?不老,他如何会死?不死,他如何会被动摇?不被动摇,他为何要渴求?
32. “所以,正是在此意义上说:‘构想的浪潮,无法席卷安住于此[根基]者,当构想的浪潮不再席卷他时,他便被称为寂静的贤者。’”
(源自 MN 140: Dhātuvibhaṅga Sutta; III 244–47)
(8)阿罗汉确实是快乐的
阿罗汉确实是快乐的!
在他们身上找不到渴爱。
“我是”的我慢已被切断,
愚痴之网已被撕裂。
他们已达到不动摇的状态,
他们的心是清澈的;
他们在这世间无所染污——
是圣者,无有诸漏。
已完全了知五蕴,
在七善法中游走,53
那些值得赞叹的优越之人
是佛陀的嫡传之子。
具足七宝,
于三学中受训,54
那些伟大的英雄们四处游方
已舍弃恐惧与战栗。
具足十种因素,
那些伟大的 nāgas,已入定,
是世间最胜的众生:
在他们身上找不到渴爱。55
无学之智已在他们心中生起:
“此身为我最后一身。”
关于梵行的核心
他们不再依赖他人。
他们在抉择中不动摇,56
他们已从再生中解脱。
已达到被调伏的阶段,
他们是世间的胜利者。
在上、横、下,
在他们身上再也找不到喜乐。
他们大胆地发出狮子吼:
“觉悟者是世间至尊。”
(源自 SN 22:76; III 83–84)
第五篇:如来
(1)佛陀与阿罗汉
“比丘们,通过对色、受、想、行、识的厌离,通过它们的褪去与寂灭,如来、阿罗汉、正等正觉者,因无执取而解脱;他被称为正等正觉者。通过对色、受、想、行、识的厌离,通过它们的褪去与寂灭,一位慧解脱的比丘,因无执取而解脱;他被称为慧解脱者。57
“比丘们,于此,如来、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与一位慧解脱的比丘之间,有什么区别、不同、差异呢?”
“尊者,我们的教法根源于世尊,由世尊引导,以世尊为依归。如果世尊能澄清此言的意义,那就太好了。比丘们听后,便会谨记在心。”
“那么,比丘们,仔细听,好好作意,我将要说了。”
“是的,尊者。”比丘们回答道。世尊这样说:
“比丘们,如来、阿罗汉、正等正觉者,是先前未生起之道的开创者,先前未产生之道的产生者,先前未宣说之道的宣说者。他是知晓道者,发现道者,善巧于道者。而他的弟子们如今循着那条道路安住,并在之后拥有它。
“比丘们,这便是如来、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与一位慧解脱的比丘之间的区别、不同、差异。”
(SN 22:58; III 65–66)
(2)为众生的福祉
“比丘们,有三种人出现于世,是为了众生的福祉,为了众生的快乐,出于对世间的慈悲,为了天人与人类的利益、福祉与快乐。是哪三种呢?
“在此,比丘们,一位如来出现于世,是阿罗汉、正等正觉者……天人之师,佛陀,世尊。他所教导的 Dhamma 初善、中善、后善,义理与言辞俱佳;他揭示了完全圆满清净的梵行。比丘们,这是第一种出现于世的人,是为了众生的福祉,为了众生的快乐,出于对世间的慈悲,为了天人与人类的利益、福祉与快乐。
“其次,比丘们,那位导师的一位弟子是阿罗汉,诸漏已尽[如经文 X,1(3), §42}……通过最终的智慧完全解脱。他所教导的 Dhamma 初善……他揭示了完全圆满清净的梵行。比丘们,这是第二种出现于世的人,是为了众生的福祉,为了众生的快乐,出于对世间的慈悲,为了天人与人类的利益、福祉与快乐。
“其次,比丘们,那位导师的一位弟子是行道中的有学,博学且具足戒行与操守。他也教导初善的 Dhamma ……他揭示了完全圆满清净的梵行。比丘们,这是第三种出现于世的人,是为了众生的福祉,为了众生的快乐,出于对世间的慈悲,为了天人与人类的利益、福祉与快乐。
“比丘们,这三种人出现于世,是为了众生的福祉,为了众生的快乐,出于对世间的慈悲,为了天人与人类的利益、福祉与快乐。”
(It 84; 78–79)
(3)舍利弗的崇高之言
尊者舍利弗 (Sāriputta) 走近世尊,向他顶礼,坐在一旁,然后说道:“尊者,我对世尊有如此的信心,我相信过去未曾有,未来也不会有,现在也不存在任何其他沙门或婆罗门,在觉悟方面比世尊更有智慧。”58
“舍利弗 (Sāriputta),你这番话真是崇高,如同呐喊,你作出了决定性的狮子吼。舍利弗 (Sāriputta),你是否以你的心,遍知过去所有已出现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的心,并如此了知:‘那些世尊具足如此的戒行,或如此的品质,或如此的智慧,或如此的禅住,或如此的解脱’?”59
“没有,尊者。”
“那么,舍利弗 (Sāriputta),你是否以你的心,遍知未来所有将出现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的心,并如此了知:‘那些世尊将具足如此的戒行,或如此的品质,或如此的智慧,或如此的禅住,或如此的解脱’?”
“没有,尊者。”
“那么,舍利弗 (Sāriputta),你是否以你的心,遍知我——现在身为阿罗汉、正等正觉者——的心,并如此了知:‘世尊具足如此的戒行,或如此的品质,或如此的智慧,或如此的禅住,或如此的解脱’?”
“没有,尊者。”
“舍利弗 (Sāriputta),既然你对过去、未来、现在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的心,没有任何遍知的智慧,为何你发出如此崇高、呐喊般的话语,并作出如此决定性的狮子吼:‘尊者,我对世尊有如此的信心,我相信过去未曾有,未来也不会有,现在也不存在任何其他沙门或婆罗门,在觉悟方面比世尊更有智慧’?”
“尊者,我虽然没有遍知过去、未来、现在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之心的智慧,但我通过对 Dhamma 的推断而了知此事。尊者,譬如,一位国王有一座边境城市,有坚固的城墙、壁垒和拱门,只有一个城门。驻守在那里的守门人聪明、能干且有智慧;他能阻止陌生人进入,并让熟人进来。当他沿着环绕城市的道路行走时,他不会在城墙上看到任何裂缝或开口,即使是小到足以让一只猫溜进去的也没有。他可能会想:‘凡是进出这座城市的大型生物,都必须通过这唯一的门进出。’
“同样地,尊者,我通过对 Dhamma 的推断而了知此事:凡是过去已出现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所有那些世尊都首先舍弃了五盖,即削弱智慧的心之杂染;然后,他们的心善安住于四念住,正确地培育了七觉支;由此,他们觉悟了无上正等正觉。而且,尊者,凡是未来将出现的阿罗汉、正等正觉者,所有那些世尊都将首先舍弃五盖,即削弱智慧的心之杂染;然后,他们的心善安住于四念住,将正确地培育七觉支;由此,他们将觉悟无上正等正觉。而且,尊者,世尊,现在身为阿罗汉、正等正觉者,首先舍弃了五盖,即削弱智慧的心之杂染;然后,他的心善安住于四念住,正确地培育了七觉支;由此,他已觉悟无上正等正觉。”
“善哉,善哉,舍利弗 (Sāriputta)!因此,舍利弗 (Sāriputta),你应该经常向比丘、比丘尼、男居士、女居士重复这一 Dhamma 的开示。即使有些愚人可能对如来存有困惑或不确定,当他们听到这一 Dhamma 开示时,他们的困惑或不确定将会被舍弃。”
(SN 47:12; V 159–61)
(4)力量与自信的根基
9. “舍利弗 (Sāriputta),如来有这十种如来力,凭借这些力量,他宣称自己居于群牛之首的地位,在集会中作狮子吼,并转动梵轮。60是哪十种呢?
10. (1) “在此,如来如实了知可能为可能,不可能为不可能。61这便是如来的一种如来力,如来凭借它,宣称自己居于群牛之首的地位,在集会中作狮子吼,并转动梵轮。
11. (2) “再者,如来通过可能性与原因,如实了知过去、未来、现在所造作业的果报。那也是一种如来力……62
12. (3) “再者,如来如实了知通往各处的道。那也是一种如来力……63
13. (4) “再者,如来如实了知世界有众多不同界。那也是一种如来力……
14. (5) “再者,如来如实了知众生有不同的倾向。那也是一种如来力……64
15. (6) “再者,如来如实了知其他众生、其他人的根之倾向。那也是一种如来力……65
16. (7) “再者,如来如实了知关于禅那、解脱、定、等至的杂染、清净与生起。那也是一种如来力……66
17. (8) “再者,如来忆念起自己众多过去生,及其各个方面与细节。那也是一种如来力……
18. (9) “再者,如来以清净超人的天眼,看见众生的死亡与再生,劣等与优等,美貌与丑陋,幸运与不幸,并了知众生如何随其业而流转。那也是一种如来力……
19. (10) “再者,通过以亲身证智为自己实现它,如来在今生今世进入并安住于心解脱、慧解脱,即随着诸漏的寂灭而无漏的解脱。那也是一种如来力,如来凭借它,宣称自己居于群牛之首的地位,在集会中作狮子吼,并转动梵轮。
20. “如来有这十种如来力,凭借这些力量,他宣称自己居于群牛之首的地位,在集会中作狮子吼,并转动梵轮。……
22. “舍利弗 (Sāriputta),如来有这四种自信的根基,67凭借它们,他宣称自己居于群牛之首的地位,在集会中作狮子吼,并转动梵轮。是哪四种呢?
23. “在此,我看不到任何理由,任何沙门、婆罗门、天人、Māra、梵天或世上任何其他人,能够依 Dhamma 指责我:‘你自称正等正觉,但你对这些事并未正等正觉。’ 因为看不到那样的理由,我安住于安稳、无畏与自信之中。
24. “我看不到任何理由,任何沙门……或任何人能够指责我:‘你自称已断尽诸漏,但你并未断尽这些漏。’ 因为看不到那样的理由,我安住于安稳、无畏与自信之中。
25. “我看不到任何理由,任何沙门……或任何人能够指责我:‘你所说的那些障碍,并不能障碍行此法者。’ 因为看不到那样的理由,我安住于安稳、无畏与自信之中。
26. “我看不到任何理由,任何沙门……或任何人能够指责我:‘当你向某人教导 Dhamma 时,当他修行时,它并不能引导他完全灭尽苦。’ 因为看不到那样的理由,我安住于安稳、无畏与自信之中。
27. “如来有这四种自信,凭借它们,他宣称自己居于群牛之首的地位,在集会中作狮子吼,并转动梵轮。”
(源自 MN 12: Mahāsīhanāda Sutta; I 70–72)
(5)大光明之显现
“比丘们,只要日月还未在世间升起,就一直没有大光明与大光辉的显现,而是盲目的黑暗笼罩,一团稠密的黑暗;只要如此,昼夜便不可辨,月与半月便不可辨,季节与年份便不可辨。但是,比丘们,当日月在世间升起时,便有大光明与大光辉的显现;那时便没有盲目的黑暗,没有稠密的黑暗;那时昼夜便可辨,月与半月便可辨,季节与年份便可辨。
“同样地,比丘们,只要如来还未在世间出现,一位阿罗汉、正等正觉者,就一直没有大光明与大光辉的显现,而是盲目的黑暗笼罩,一团稠密的黑暗;只要如此,四圣谛就无从解释、教导、宣说、建立、揭示、分析或阐明。但是,比丘们,当如来在世间出现,一位阿罗汉、正等正觉者,那时便有大光明与大光辉的显现;那时便没有盲目的黑暗笼罩,没有稠密的黑暗;那时便有对四圣谛的解释、教导、宣说、建立、揭示、分析与阐明。”
(SN 56:38; V 442–43)
(6)期望我们利益之人
25. “比丘们,譬如在一片林地里,有一片广大的低洼沼泽,附近住着一大群鹿。这时来了一个人,意图毁坏、伤害和束缚它们,他便封锁了那条安全、良好、可快乐行走的道路,另开辟了一条假路,并放下一个诱饵,设下一个假人,以便那大群鹿日后会遭遇灾祸、不幸和损失。但另一个人来了,意图为它们带来利益、福祉和保护,他便重新开启了那条安全、良好、可快乐行走的道路,封锁了假路,移除了诱饵,摧毁了假人,以便那大群鹿日后能成长、增益和圆满。
26. “比丘们,我用这个譬喻是为了传达一个意义。这个意义是:‘广大的低洼沼泽’是欲乐的代名词。‘大群鹿’是众生的代名词。‘意图毁坏、伤害和束缚它们的人’是恶魔 Māra 的代名词。‘假路’是邪八正道的代名词,即:邪见、邪思惟、邪语、邪业、邪命、邪精进、邪念、邪定。‘诱饵’是喜悦和贪欲的代名词。‘假人’是无明的代名词。‘意图为它们带来利益、福祉和保护的人’是如来、阿罗汉、正等正觉者的代名词。‘安全、良好、可快乐行走的道路’是八正道的代名词,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所以,比丘们,那条安全、良好、可快乐行走的道路已被我重新开启,邪路已被封锁,诱饵已被移除,假人已被摧毁。”
(源自 MN 19: Dvedhāvitakka Sutta; I 117–18)
(7)狮子
“比丘们,傍晚时分,兽中之王狮子从它的巢穴出来。然后它伸展身体,环顾四周,作狮子吼三次,之后便出发觅食。
“当兽中之王狮子作狮子吼时,大多数听到声音的动物都充满了恐惧、紧迫感和惊骇。住在洞穴里的进入洞穴;住在水里的进入水里;住在林子里的进入林子里;鸟儿则飞上天空。即使是在村庄、城镇和都城里被坚固绳索捆绑的皇家公象,也会挣脱并弄断它们的束缚;它们惊恐万分,大小便失禁,四处逃窜。比丘们,兽中之王狮子在动物中就是如此有力量,如此威严和强大。
“同样地,比丘们,当如来出现于世,一位阿罗汉、正等正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陀,世尊,他如此教导 Dhamma:‘色是如此,其生起是如此,其息灭是如此;受是如此……想是如此……行是如此……识是如此,其生起是如此,其息灭是如此。’
“那时,比丘们,那些长寿、美丽、充满快乐、长久居住在高耸宫殿中的天人,听到如来教导的 Dhamma 时,大多数68都充满了恐惧、紧迫感和惊骇,[说道]:‘看来,虽然我们自认为是常,但我们是无常的;看来,虽然我们自认为是稳固,但我们是不稳固的;看来,虽然我们自认为是永恒,但我们是短暂的。看来,尊者,我们是无常的、不稳固的、短暂的,被包含在身见之内。’69 比丘们,如来对这个世界连同其天人就是如此有力量,如此威严和强大。”
(SN 22:78: III 84–85)
(8)他为何被称为如来?
“比丘们,世界已被如来完全觉悟;如来已从世界中离执。世界的集起已被如来完全觉悟;如来已舍弃世界的集起。世界的寂灭已被如来完全觉悟;如来已实证世界的寂灭。通往世界寂灭之道已被如来完全觉悟;如来已培育了通往世界寂灭之道。
“比丘们,在这世界,连同其天人、Māra、梵天,在这芸芸众生,连同其沙门、婆罗门、天人与人类之中,凡所见、闻、觉、知、触、求、意所察的一切,皆已被如来所觉悟;因此他被称为如来。
“比丘们,从他完全觉悟的那一夜,直到他证入最终 Nibbāna 的那一夜,在此期间,他所说、所谈、所阐述的一切,皆是如是,而非他样;因此他被称为如来。
“比丘们,他如其所说而行;如其所行而说。因为他如说而行,如行而说,因此他被称为如来。
“比丘们,在这世界,连同其天人、Māra、梵天,在这芸芸众生,连同其沙门、婆罗门、天人与人类之中,如来是征服者、不被征服者、遍见者、主宰者;因此他被称为如来。”
亲身了知一切世界,
世间一切如其本来,
他从一切世界离执,
不涉入一切世界。
他确实是征服一切的贤者,
从一切结缚中解脱者,
已达到至上寂静之境,
Nibbāna,无有任何畏惧。
他是佛陀,诸漏已尽,
无有烦扰,一切疑虑已断,
已达到一切 kamma 的寂灭,
在各种获取的灭尽中解脱。
他是世尊,是佛陀,
他是雄狮,无与伦比,
在这个世界连同其天人之中,
他转动了梵轮。
因此那些天人与人类
已皈依佛陀,
聚集一起,向他致敬,
这位伟大而无所畏怯者。
“已调伏者,他是调伏者中的至尊;
寂静者,他是带来和平者中的贤者;
已解脱者,他是使人解脱者中的首领;
已度脱者,他是度脱者中的最胜者。”
因此他们确实如此向他致敬,
这位伟大而无所畏怯者。
在这个世界连同其天人之中,
无人能与您匹敌。
(AN 4:23; II 23–24 = It 112; 121–23)
注释
-
“道”与“果”的术语是义注的区分方式。诸经本身不使用四“道”的架构,而只说一道,即导向苦灭的八正道。这也被称为 arahattamagga,即阿罗汉道,但这是广义上的,指通往最高目标的道路,而非狭义上指在阿罗汉果之前的道。然而,诸经确实区分了为证得某一特定果而修行的人 (phala-sacchikiriyāya paṭipanna) 和已证得此修行所致阶段的人(见第十章第一篇(1))。基于此区别,义注中道与果的术语,作为简洁指代尼柯耶架构中两个阶段的方式,是很有用的。 ↩
-
我对一来者减弱贪、嗔、痴的解释是基于义注的。除了标准的公式外,诸经本身对一来者所说的很少。 ↩
-
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诸经暗示法随行者和信随行者会持续这样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诸经的立场似乎与义注的观点相矛盾,后者认为证道者只在一个心识刹那中是证道者。如果后者为真,这将意味着法随行者和信随行者只在一个心识刹那中是如此,这似乎难以与经文中所述他们接受供养、前往森林中的住所等陈述相协调。 ↩
-
义注的解释方法规定,禅修者从禅定中出定,并以通过禅那而变得敏锐和柔软的心来修习观禅。然而,诸经本身并未提及从禅定中出定。如果只读诸经而不读义注,禅修者似乎是在禅定之内审视诸禅支。 ↩
-
由于阿罗汉已从轮回中解脱,不可能指出他们在轮回中的任何地方可能会出现;因此他们没有未来的轮回显现。 ↩
-
“五下分结” (pañc’ orambhāgiyāni saṃyojanāni) 是:身见、疑、戒禁取、欲贪和嗔恚。化生者 (opapātika) 的再生不依赖于父母。 ↩
-
“三结”是上述五结中的前三结。“定于命运”(niyata) 意指入流者注定最多在人间或天界再经历七次生命后即可达到解脱。菩提 (sambodhi) 是阿罗汉对四圣谛的圆满最终了知。 ↩
-
关于这两种类型的区别,见下文,第十章第一篇(5) §§20–21 和第十章第二篇(2)。 ↩
-
《疏钞》说这指的是致力于修习观禅的人,他们尚未达到任何出世间的证悟,但对佛法的真理有坚固的信念。saddhāmattaṃ pemamattaṃ 这两个词或许可以译为“仅仅是信,仅仅是爱”,但这样的品质无法保证能往生天界。因此,似乎有必要将后缀-matta 理解为意指足够数量的这些品质,而不仅仅是它们的存在。 ↩
-
佛陀在此正与游方者婆蹉衢多 (Vacchagotta) 交谈(见第九章第五篇(6))。《疏钞》说婆蹉衢多认为佛陀可能是其僧团中唯一达到最终目标的人。 ↩
-
这个问题以及 §11 中的问题都与不来者有关。请注意不来者遵守梵行。 ↩
-
这个问题以及 §12 中的问题都与入流者和一来者有关。因为他们被描述为享受感官之乐,这意味着他们不必遵守梵行。 ↩
-
Ubhatobhāgavimutta。《疏钞》:他以两种方式解脱,因为他通过无色定从色身中解脱,并通过阿罗汉道从名身中解脱。“俱解脱”阿罗汉的双重解脱,不应与“无漏心解脱、慧解脱” (anāsavā cetovimutti paññāvimutti) 相混淆,后者是所有阿罗汉所共有的,无论他们是否证得无色定。 ↩
-
Paññāvimutta。《疏钞》说这包括那些证得四禅中任何一禅的人以及纯观阿罗汉。在尼柯耶中没有明确承认纯观阿罗汉。 ↩
-
Kāyasakkhī。这包括从阿罗汉道上的行者到证得无色定的入流者的所有人。 ↩
-
Diṭṭhippatta。这包括那些未证得无色定,且以慧为主导根的同类行者。 ↩
-
Saddhāvimutta。这包括那些以信为主导根的同类行者。 ↩
-
Dhammānusārī。这类以及下一类信随行者 (saddhānusārī),是为证悟入流果而修行的两种人。见第375页和第十章第二篇(2)。 ↩
-
Sammattaniyāma:出世间的八正道。 ↩
-
与义注相反,义注认为证道者在证道后立即证果,而尼柯耶只说达到法随行者或信随行者阶段的人(相当于义注的证道者概念)将在今生之内证果——但未必在下一个心识刹那。这两种立场或许可以调和,如果我们把法随行者和信随行者的道看作是时间上延续的,但在一个瞬间的突破中达到高潮,并立即随之证果。 ↩
-
这段陈述清楚地说明了入流者与入流道上行者的区别。信随行者是凭信任接受教法(带有有限程度的理解),法随行者是通过审察接受它(带有更大程度的理解);但入流者已亲身了知和彻见了教法。 ↩
-
现观法 (dhammābhisamaya) 和获得法眼 (dhammacakkhupaṭilābha) 是同义词,意指证得入流。 ↩
-
Aveccappasāda。义注将其解释为通过已证得的,即入流,而获得的不动摇的信心。 ↩
-
地狱、畜生界和饿鬼界本身就是苦界、恶趣和下界。 ↩
-
身 (sakkāya) 是我们认同为“自我”的五蕴的组合。身的息灭是涅槃。 ↩
-
Upadhi。在当前语境中,这个词似乎意指物质财富。 ↩
-
在这十一个属性中,“无常”和“坏灭”阐明了无常的特性;“异”、“空”和“无我”阐明了无我的特性;其他六个则阐明了苦的特性。 ↩
-
《疏钞》:他将心从禅那中所包含的五蕴上移开,他已见到五蕴被标以三法印。“不死界” (amatadhātu) 是涅槃。首先,他听闻涅槃被赞誉为“寂静、殊胜”等等,便以观智“将心导向它”。然后,他以出世间道,“将心导向它”,即以涅槃为所缘,并彻见其为“寂静、殊胜”等等。 ↩
-
Dhammarāgena dhammanandiyā。这种对法的欲求和对法的喜悦似乎同时做了两件事:(1) 因为它们是指向法的,它们推动弟子去断除五下分结;(2) 因为它们仍然是欲求和喜悦,它们阻碍了阿罗汉果的证得。 ↩
-
这里,在无色定中,经文只提到了四名蕴。色蕴被排除了。 ↩
-
这些是导致厌离和离欲的禅修业处。身体的不净观在第八章,8 §10;食物的厌恶想在《清净道论》341–47页(Ppn 11:1–26)有解释;死随念在《清净道论》229–39页(Ppn 8:1–41);对一切世间的不乐想,以及对一切行的无常随观,在《增支部》10:60;V 111。 ↩
-
在《增支部》V 110中,舍离想 (pahānasaññā) 被解释为去除染污的念头。在《增支部》V 110–11中,离欲想 (virāgasaññā) 和息灭想 (nirodhasaññā) 都被解释为对涅槃属性的思惟。 ↩
-
义注将中般涅槃者 (antarāparinibbāyī) 解释为生于净居天,在寿命的前半段证得阿罗汉果的人。这一类型又被细分为三种,取决于阿罗汉果是在何时证得:(1) 在再生的当天;(2) 经过一两百劫后;或 (3) 经过四百劫后。生般涅槃者 (upahaccaparinibbāyī) 被解释为在度过寿命的前半段后证得阿罗汉果的人。对于义注来说,无行般涅槃者 (asaṅkhāraparinibbāyī) 和有行般涅槃者 (sasaṅkhāraparinibbāyī) 随后成为前两类不来者证得目标时的两种模式,即分别以轻易、无须强烈努力,以及以困难、须强烈努力的方式证得。然而,对前两种类型的这种解释忽略了其名称的字面意义,也推翻了在诸经其他地方所描绘的五种类型的次第性和互斥性。如果按字面意思理解中般涅槃者,它似乎应该指在两世之间,或许是以微细身存在于中阴身时证得涅槃的人。生般涅槃者则成为在新生命中“着陆”或“触地”时,即几乎在再生后立即证得涅槃的人。接下来的两个术语指在下一生中证得阿罗汉果的两种类型,区别在于他们为赢得目标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程度。最后一种,上流至色究竟天者 (uddhaṃsota akaniṭṭhagāmī),是在相继的净居天中再生,在每一处都活满全部寿命,并最终在色究竟天界(最高的净居天)证得阿罗汉果的人。此解释虽然与巴利义注相反,但似乎得到了《增支部》7:52 (IV 70–74) 的证实,其中燃木片的譬喻表明这七种类型(包括三种中般涅槃者)是互斥的,并且是根据其根的利钝程度来分级的。 ↩
-
差摩 (Khemaka) 宣称他在五蕴中不承认有我或我所,这含蓄地表明他至少已证得入流者的层次。但其他比丘没有意识到所有圣者都共有此理解,而误以为这是阿罗汉独有的证悟。因此他们将差摩 (Khemaka) 的话曲解为暗示他已证得阿罗汉果。 ↩
-
虽然我查阅的《相应部》所有三个版本(缅甸版、锡兰版和欧洲版)以及《义注》的两个版本(缅甸版和锡兰版)都读作 asmī ti adhigataṃ,但我怀疑这是一个已经通行的古老讹误。我建议读作 asmī ti avigataṃ。这段经文阐明了有学者 (sekha) 与阿罗汉之间的本质区别。有学者虽已断除身见,因此不再认同五蕴中的任何一蕴为我,但他尚未根除无明,无明维持着一种残余的我慢和“我是”的欲求 (anusahagato asmī ti māno asmī ti chando),这与五蕴有关。相比之下,阿罗汉已根除无明,即一切误解的根源,因此不再怀有任何“我”和“我所”的观念。其他长老显然尚未证得任何觉悟阶段,因此不理解这种区别,但尊者差摩 (Khemaka) 必定至少是入流者(一些义注师说他是不来者),因此知道断除身见并不能完全去除个人认同感。即使对于不来者,基于五蕴的“主体性气味”仍然萦绕于他的体验中。 ↩
-
义注:凡夫的心识过程就像脏布。三随观(无常、苦、无我)就像三种清洁剂。不来者的心识过程就像用三种清洁剂洗过的布。阿罗汉道所要根除的烦恼就像清洁剂的残余气味。阿罗汉道的智慧就像芳香的箱子,而由该道断除一切烦恼则像布放入箱子后,清洁剂的残余气味消失一样。 ↩
-
也就是说,在佛陀的教法之外。 ↩
-
据我理解,“那是他们的归宿……他们的最终目标”即是涅槃。我们在此看到了有学者与阿罗汉之间的另一个本质区别:有学者见到涅槃,即五根的归宿,它们所达到的顶点,它们的果实与最终目标;然而,他无法“身触之”,无法进入对它的圆满体验。相比之下,阿罗汉既见到了最终目标,也能于当下圆满地体验它。 ↩
-
这就是三十七道品 (bodhipakkhiyā dhammā),字面意思是“与觉悟相关的法”,更通俗地说:“助觉悟法”。关于四念住,详见第七章,2 和第八章,8 及《相应部》第47章。四正勤等同于正精进,详见第七章,2 及《相应部》第49章。四神足是:以 (1) 欲,或 (2) 精进,或 (3) 心,或 (4) 观为基础的定,伴随着精进的意愿力;见《相应部》第51章。五根在第十章,1(2);详见《相应部》第48章。五力与五根是相同的五个因素,但力量更强。七觉支在第八章,9;见《相应部》第46章。八正道在第七章,2;见《相应部》第45章。 ↩
-
《疏钞》将其认定为第四禅的舍。 《疏钞》说晡古萨帝 (Pukkusāti) 已经证得第四禅,并对此深深执着。佛陀首先赞扬这种舍以激发晡古萨帝 (Pukkusāti) 的信心,然后逐渐引导他证得无色定以及出世间的道与果。 ↩
-
意思是:如果他证得空无边处,并在仍然对其执着的情况下逝世,他将再生于空无边处,并将在那里活满该界所规定的两万劫的全部寿命。在更高的三个无色界中,寿命据说分别为四万劫、六万劫和八万四千劫。 ↩
-
《疏钞》:这样说是为了显示无色定中的危险。通过“此乃有为”这一句话,他显示了:“虽然那里的寿命是两万劫,但它是有为的、被造作的、被构建的。因此它是无常的、不稳定的、不持久的、短暂的。它会消亡、破碎、坏灭;它牵涉到生、老、死,建立在苦之上。它不是庇护所,不是安全之地,不是皈依处。凡夫在那里逝世后,仍然可能再生于四恶趣。” ↩
-
So n’eva abhisaṅkharoti nābhisañcetayati bhavāya vā vibhavāya。这两个动词暗示了意愿作为一种构建和维持有为存在的建设性力量的概念。停止对有或无有的意愿,显示了对永恒存在和断灭的渴爱的熄灭。 ↩
-
《疏钞》说,此时晡古萨帝 (Pukkusāti) 彻见了三道三果,成为一名不来者。他意识到他的老师就是佛陀本人,但他无法表达这一证悟,因为佛陀继续他的开示。 ↩
-
这段经文展示了阿罗汉安住于有余涅槃界 (sa-upādisesa nibbānadhātu);见第九章第五篇(5)。虽然他继续体验感受,但他对乐受无贪,对苦受无嗔,对不苦不乐受无痴。 ↩
-
也就是说,他仅在身体及其命根持续时才继续体验感受,但不会超越于此。 ↩
-
这指的是他证得无余涅槃界 (anupādisesa nibbānadhātu)——即随着他的最终般涅槃,一切有为存在的息灭。见第九章第五篇(5)。 ↩
-
这完成了第一基础,即慧基 (paññādhiṭṭhāna) 的阐述。《疏钞》说,一切苦灭尽之智是与阿罗汉果相关的智慧。 ↩
-
《疏钞》在此提到四种取 (upadhi):五蕴;烦恼;行;以及感官之乐。 ↩
-
“我慢之潮” (maññussavā),如下一段将显示的,是源于我慢三根——爱、慢、见的思想和观念。“寂静的牟尼” (muni santo) 是阿罗汉。 ↩
-
“我将是”和“我将不是”的想法,暗示了常见(死后继续存在)和断见(死后个人断灭)的观点。有色和无色的选项代表了来世存在的两种模式,即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想等三者则是来世存在的另外三种模式,以其与想或觉知的关系来区分。 ↩
-
在他身上不存在的是有爱,它会导致死后新的出生。 ↩
-
Satta saddhammā。信、惭、愧、多闻、精进、念和慧。例如见《中部》53.11–17。 ↩
-
增上戒学、增上心学和增上慧学。 ↩
-
十个因素是八正道的八个道支,补充以正智和正解脱。例如见《中部》65.34和《中部》78.14。 ↩
-
三重分别:“我更优”、“我相等”、“我更差”。 ↩
-
此处的 bhikkhu paññāvimutto 很有可能应被理解为任何阿罗汉弟子,而非特指与 ubhatobhāgavimutta 阿罗汉相对的 paññāvimutta。 ↩
-
这部经被包含在《大般涅槃经》中(在《长部》II 81–83),但没有最后一段。一个更为详尽的版本构成了《长部》28。 ↩
-
义注将“如是品质” (evaṃdhammā) 认定为“与定相关的品质” (samādhipakkhā dhammā)。 ↩
-
十如来力是智力。在《分别论》§§808–31中有详细分析。“梵轮”即是法轮。 ↩
-
详情见《中部》115.12–19。 ↩
-
《疏钞》解释处 (ṭhāna) 为领域、环境、时间及努力,这些因素既可能阻碍也可能加强结果。因 (hetu) 是业本身。佛陀的这种智慧由第五章,1(1)–(3) 的经文所阐明。 ↩
-
这表示佛陀了知导向轮回中所有未来归宿以及最终解脱的各类行为。见《中部》12.35–42。 ↩
-
《分别论》§813解释说,他了知众生有劣等和优等的倾向,并且众生自然会与有相似倾向的众生交往。 ↩
-
《分别论》§§814–27 给出了详细的分析。《疏钞》更简洁地陈述说,他了知其他众生五根的优劣倾向。 ↩
-
《分别论》§828:杂染 (saṅkilesa) 是导致衰退的因素;清净 (vodāna) 是导致卓越的因素;出离 (vuṭṭhāna) 既是清净也是从定中出定。八解脱 (vimokkha) 见于《长部》15.35,《长部》16.3.33,《中部》77.22,《中部》137.26等;九次第定 (samāpatti) 是四禅、四无色定以及想受灭尽定。 ↩
-
Vesārajja。《疏钞》说这是当他反思自己在四种情况下没有畏惧时,心中生起的喜悦之智的名称。 ↩
-
义注说,作出这个限定是为了排除那些是圣者的天人。 ↩
-
义注:身见所摄 (sakkāyapariyāpannā):包含在五蕴之内。当佛陀教导他们被三法印所印证的法,揭示轮回中的过患时,智惧便进入他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