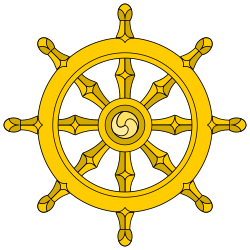Index
第七章:解脱之道

导言
在本章中,我们将探讨佛陀教法独特而卓越的特征,即其“出世间” (lokuttara) 的解脱之道。这条道路建立在我们对感官之乐的危殆、死亡的必然性以及轮回的残酷本质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转变后的理解之上,这些主题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探讨过。它的目标是引导修行者达到超越一切有为存在领域的解脱状态,达到佛陀自己在觉悟之夜所证得的、无忧无染的涅槃之乐。
本章呈现的经文,对佛陀的出世间道提供了一个宏观的概览;接下来的两章将汇集更侧重于心之训练和智慧培育的经文,这是出世间道的两大分支。然而,我首先以几部旨在阐明这条道路之目的的经文作为开始,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阐释。第七章第一篇(1)的《教诫摩罗迦子短经》(MN 63),显示了佛法之道并非为了给哲学问题提供理论答案。在这部经中,摩罗迦子 (Māluṅkyāputta) 比丘找到佛陀,要求回答十个臆测性问题,并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就要离开僧团。学者们曾争论佛陀拒绝回答这类问题是因为它们原则上无法回答,还是仅仅因为它们与实际解决苦的问题无关。《相应部》中的两组经文——SN 33:1–10 和 SN 44:7–8——清楚地表明,佛陀的“沉默”有比单纯的务实考量更深的基础。这些经文显示,所有这类问题都基于一个潜在的假设,即存在应通过一个“自我”以及该自我所处的世界来解释。由于这些前提是无效的,任何基于这些前提构建的答案都不可能是有效的,因此佛陀必须拒绝这些问题本身。
然而,尽管佛陀有哲学上的理由拒绝回答这些问题,他也因为认为沉迷于其解答与寻求离苦无关而拒绝它们。这个理由在《教诫摩罗迦子经》中显而易见,其中著名的“毒箭喻”便说明了这一点。佛陀说,无论这些观点中任何一个是真是假,“都有生,有老,有死,有愁、悲、苦、忧、恼,我在此刻当下所教导的是它们的寂灭。”对照上一章末尾所描绘的轮回背景,这句话现在具有了更广阔的意义:“生、老、死的寂灭”不仅是一生中苦的终结,更是我们在轮回无数劫中所经历的、无法估量的重复生、老、死之苦的终结。
第七章第一篇(2)的《心材喻大经》(MN 29),从另一个角度阐明了佛陀阐述其出世间法的目的。该经讲述了一位“族姓子”为了达到苦的尽头,从家庭生活出家到无家。尽管在受戒时目标真诚,但一旦他取得一些成就,无论是像获得利养和名誉这样的较低成就,还是像获得定和观智这样的较高成就,他便变得自满,并忽略了他走上佛陀之道的初衷。佛陀宣称,这些沿途的站点——无论是戒行、定力,甚或是知见——都不是修行生活的最终目标。其目标,即其心材或根本目的,是“不动心解脱”,他敦促那些已踏上此道的人不要满足于任何次于此的目标。
第七章第一篇(3)选自《道相应》。这些经文指出,在佛陀座下修习梵行的目的,是“贪欲的消退……无取着的最终涅槃”,而八正道正是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
八正道是解脱之道的经典表述,这从佛陀的初转法轮经中已经很清楚,他在其中称八正道是通向苦灭之道。第七章第二篇给出了各道支的正式定义,但没有具体展示如何将其修行融入弟子的生活中。具体的应用将在本章以及第八、第九章中详细阐述。
第七章第三篇以一种我们不习惯在标准佛法宣讲中听到的方式,为解脱之道提供了不同的视角。虽然我们常被告知,佛法之道的修习完全依赖于个人努力,但这部经文强调了善友的重要性。佛陀宣称,善友不仅是“修行生活的一半”,而是其全部,因为追求精神圆满的努力并非纯粹的独行事业,而是依赖于亲密的个人关系。善友为法的修习赋予了不可或缺的人性维度,并将佛教修行者的团体塑造成一个社群,通过师生关系纵向连结,并通过同道间的友谊横向连结。
与一个普遍的假设相反,八个道支并非要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地修习的步骤。将它们描述为“组成部分”比“步骤”更为恰当。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所有八个道支应同时存在,各自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就像一根由八股绳索编织而成的缆绳,使其强度达到最大。然而,在达到那个阶段之前,道的诸支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顺序。八个道支通常分为三组,如下:1. 戒蕴 (sīlakkhandha),由正语、正业、正命组成;2. 定蕴 (sam̄dhikkhandha),由正精进、正念、正定组成;3. 慧蕴 (paññākkhandha),由正见、正思惟组成。
然而,在《尼柯耶》中,这种关联只出现过一次(在 MN 44; I 301),并且被认为是昙摩提那 (Dhammadinnā) 比丘尼而非佛陀本人所说。可以说,两个慧支被放在开头,是因为在道的起点需要初步的正见和正思惟,正见提供对佛法原则的概念性理解,以指导其他道支的发展,正思惟则为道的发展提供正确的动机和方向。
在《尼柯耶》中,佛陀常将道的修习阐述为一种从第一步到最终目标的渐进式训练 (anupubbasikkhā)。这种渐进式训练是戒、定、慧三学的更精细划分。在经文中,渐进式训练的阐述总是以出家至无家,并采纳比丘(佛教僧侣)的生活方式开始。这立即提醒我们,在佛陀的务实愿景中,僧侣生活的重要性。原则上,八正道的完整修习对任何生活方式的人开放,无论是僧侣还是居士,佛陀也证实他的许多在家弟子在法上有所成就,并已证得四种觉悟阶段的前三种,达到不来果(阿那含);南传上座部的义注家们说,在家弟子也可以证得第四个阶段,即阿罗汉果,但他们要么在临死前证得,要么在证得后立即寻求出家。然而,事实仍然是,在家的生活不可避免地会滋生许多世俗的关切和个人的执着,这些都会妨碍一心一意寻求解脱的道路。因此,当佛陀自己踏上他崇高的探索之路时,他选择了出家到无家,在他觉悟之后,作为帮助他人的一个实际方法,他建立了僧团,即比丘和比丘尼的僧团,为那些希望不受家庭生活烦扰、全身心投入法的人们而设。
渐进式训练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长部》中的长版本,另一种是《中部》中的中等长度版本。主要区别在于:(1)长版本对与僧侣礼仪和苦行自制相关的戒律有更详细的论述;(2)长版本包含八种神通,而中等长度版本有三种。然而,由于这三种是佛陀在他自己觉悟的记述中提到的(见第二章第三篇(2)),它们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长版本渐进式训练的主要范例见于 DN 2;中等长度版本见于 MN 27 和 MN 51,变体见于 MN 38、MN 39、MN 53、MN 107 和 MN 125。此处,第七章第四篇收录了 MN 27 的全文,该经将训练嵌入了赋予其名称的象足迹喻中。第七章第五篇,节选自 MN 39,重复了 MN 27 中描述的训练的更高阶段,但包含了后者未包含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譬喻。
这个序列以一位如来 (Tathāgata) 出现于世间并阐述法为开端。听闻此法后,弟子生起信心,追随导师出家。然后,他受持戒律,以促进品行的清净和苦行者的正命。接下来的三个步骤——知足、防护诸根、正念正知——将净化过程内化,从而架起了从戒行到定的过渡桥梁。
关于断除五盖的部分,涉及定的初步训练。五盖——欲欲、瞋恚、昏沉睡眠、掉举恶作、疑——是禅修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必须去除它们,心才能变得专注统一。关于渐进式训练的固定段落只对克服五盖做了纲要性的处理,但《尼柯耶》中的其他文本提供了更实用的指导,而巴利义注则提供了更多细节。MN 39 版本中的譬喻——见第七章第五篇——说明了通过克服五盖所赢得的喜悦的自由感。
序列的下一阶段描述了禅那 (jhānas) 的证得,这是一种深度的定境,心在其中完全专注于其所缘。佛陀列举了四种禅那,简单地以其在系列中的数字位置命名,每一种都比前一种更微细、更崇高。禅那总是用相同的公式来描述,在几部经中,这些公式又被极美的譬喻所补充;同样,请参见第七章第五篇。虽然智慧而非定是证得觉悟的关键因素,但佛陀在渐进式训练中总是包含禅那,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它们有助于道的内在圆满;其次,因为它们所引生的深度专注,可以作为观智生起的基础。佛陀称禅那为“如来的足迹”(MN 27.19-22),并显示它们是训练终点涅槃之乐的先驱。
从第四禅那开始,有三种可能的进一步发展路线。在渐进式训练的固定段落之外的一些文本中,佛陀提到了四种禅定状态,它们延续了由禅那建立起来的心一境性。这些状态被描述为“寂静、无色的解脱”,是定的进一步提纯。它们与禅那的区别在于超越了作为禅那所缘的微细心相,它们被命名为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和非想非非想处。
第二条发展路线是获得超常的知识。佛陀经常提到一组六种类型,后来被称为六神通 (chaḷabhiññā)。其中最后一种,即漏尽智,是“出世间”的,因此标志着第三条发展路线的顶峰。但其他五种都是世间的,是在第四禅那中达到的异常强大的心专注力的产物:神变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和天眼通(见第八章第四篇)。
禅那和无色定本身并不能导致觉悟和解脱。虽然它们崇高而寂静,但只能压制维持生死轮回的烦恼,而不能根除它们。要从最根本的层面根除烦恼,从而达到觉悟和解脱,禅修过程必须导向第三条发展路线。这就是对“诸法实相”的观照,它会导致对存在本质越来越深的洞见,并最终达到最终目标,即证得阿罗汉果。
这条发展路线是佛陀在关于渐进式训练的段落中所遵循的。他在前面描述了两种神通:宿命通和天眼通。这三者在佛陀自己的觉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三篇(2)中所见——并被合称为三明 (tevijjā)。虽然前两者对于实现阿罗汉果并非必不可少,但佛陀可能在这里包含它们,因为它们揭示了轮回中苦的真正广阔而深刻的维度,从而为穿透四圣谛做好心理准备,通过四圣谛,苦被诊断和克服。
关于渐进式训练的段落并没有明确展示禅修者发展观智的观照过程。整个过程只是通过提及它的最终成果来暗示,即漏尽智 (āsavakkhayañāṇa)。漏 (āsavas) 是对烦恼的一种分类,从其维持生死过程向前发展的角色来考量。义注家们将这个词的词源追溯到意为“流动”的词根 su。学者们对于前缀 ā 所暗示的流动是向内还是向外有不同意见;因此有些人将其译为“流入”或“影响”,另一些人则译为“流出”或“漏出”。经文中的一个固定段落独立于词源学,揭示了这个词的真正意义,它将漏描述为“能污染、带来再生、引起麻烦、在苦中成熟、并导致未来生、老、死的状态”(MN 36.47; I 250)。因此,其他翻译者绕过字面意思,将其译为“溃疡”、“腐败”或“染污”。《尼柯耶》中提到的三漏分别是对欲乐的渴爱、对存在的渴爱和无明的同义词。当弟子的心通过完成阿罗汉道而从诸漏中解脱时,他回顾自己新获得的自由,并发出他的狮子吼:“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第一篇:为何要走上修行之道?
(1)生、老、死之箭
1.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舍卫城 (Sāvatthī) 给孤独园 (Anāthapiṇḍika’s Park) 的祇树林 (Jeta’s Grove)。
2. 那时,尊者摩罗迦子 (Māluṅkyāputta) 独自禅坐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念头:
“这些臆测的观点,世尊未曾宣说、搁置、拒绝,即:‘世界是永恒的’和‘世界不是永恒的’;‘世界是有限的’和‘世界是无限的’;‘灵魂与身体是同一的’和‘灵魂是一回事,身体是另一回事’;以及‘如来死后存在’和‘如来死后不存在’和‘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和‘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1 世尊不向我宣说这些,我不赞同也不接受这个事实,所以我要去见世尊,问他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他向我宣说‘世界是永恒的’……或者‘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那么我将在他座下修习梵行;如果他不向我宣说这些,那么我将放弃修行,还俗过低等的生活。”
3. 于是,傍晚时分,尊者摩罗迦子从禅坐中起来,去到世尊那里。顶礼之后,他坐在一旁,对世尊说:
“尊者,我独自禅坐时,心中生起了这样的念头:‘这些臆测的观点,世尊未曾宣说……如果他不向我宣说这些,那么我将放弃修行,还俗过低等的生活。’如果世尊知道‘世界是永恒的’,请世尊向我宣说‘世界是永恒的’;如果世尊知道‘世界不是永恒的’,请世尊向我宣说‘世界不是永恒的’。如果世尊既不知道‘世界是永恒的’,也不知道‘世界不是永恒的’,那么对于一个不知不见的人来说,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知不见’,这是很坦率的。
“如果世尊知道‘世界是有限的’……‘世界是无限的’……‘灵魂与身体是同一的’……‘灵魂是一回事,身体是另一回事’……‘如来死后存在’……‘如来死后不存在’……如果世尊知道‘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请世尊向我宣说;如果世尊知道‘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请世尊向我宣说。如果世尊既不知道‘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也不知道‘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那么对于一个不知不见的人来说,直截了当地说:‘我不知不见’,这是很坦率的。”
4. “那么,摩罗迦子,我何曾对你说过:‘来吧,摩罗迦子,在我座下修习梵行,我将向你宣说“世界是永恒的”……或者“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没有,尊者。”——“你又何曾对我说过:‘我将在世尊座下修习梵行,而世尊将向我宣说“世界是永恒的”……或者“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没有,尊者。”——“既然如此, misguided man,你是谁,你又在放弃什么?
5. “如果有人这样说:‘除非世尊向我宣说“世界是永恒的”……或者“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否则我不在世尊座下修习梵行’,那这些问题仍将不被如来宣说,而那个人在此期间就会死去。摩罗迦子,譬如有人被一支涂满剧毒的箭射中,他的朋友和同伴,他的亲属,带了一位外科医生来为他治疗。那人却说:‘我不让这位外科医生拔出这支箭,除非我知道伤我的人是刹帝利、婆罗门、商人还是工匠。’他又会说:‘我不让这位外科医生拔出这支箭,除非我知道伤我的人的姓名和家族;……除非我知道伤我的人是高是矮,还是中等身材;……除非我知道伤我的人是黑皮肤、棕皮肤,还是金皮肤;……除非我知道伤我的人住在哪个村庄、城镇或城市;……除非我知道伤我的弓是长弓还是弩;……除非我知道伤我的弓弦是纤维、芦苇、筋、麻还是树皮做的;……除非我知道伤我的箭杆是野生的还是栽培的;……除非我知道伤我的箭杆上装的是哪种羽毛——是秃鹫、苍鹭、鹰、孔雀还是鹳的羽毛;……除非我知道伤我的箭杆是用哪种筋绑的——是牛、水牛、鹿还是猴子的筋;……除非我知道伤我的是哪种箭头——是尖刺形、剃刀形、弯曲形、倒钩形、犊齿形还是柳叶刀形。’
“这一切那人仍然不知道,而在此期间他就会死去。同样地,摩罗迦子,如果有人这样说:‘除非世尊向我宣说:“世界是永恒的”……或者“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否则我不在世尊座下修习梵行’,那这些问题仍将不被如来宣说,而那个人在此期间就会死去。
6. “摩罗迦子,如果持有‘世界是永恒的’这种观点,梵行就无法修习;如果持有‘世界不是永恒的’这种观点,梵行也无法修习。无论持有‘世界是永恒的’观点,还是‘世界不是永恒的’观点,都有生,有老,有死,有愁、悲、苦、忧、恼,我在此刻当下所教导的是它们的寂灭。
“如果持有‘世界是有限的’……‘世界是无限的’、‘灵魂与身体是同一的’……‘灵魂是一回事,身体是另一回事’……‘如来死后存在’……‘如来死后不存在’的观点,梵行就无法修习……如果持有‘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观点,梵行就无法修习;如果持有‘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的观点,梵行也无法修习。无论持有‘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观点,还是‘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的观点,都有生,有老,有死,有愁、悲、苦、忧、恼,我在此刻当下所教导的是它们的寂灭。
7. “因此,摩罗迦子 (Māluṅkyāputta),记住我未曾宣说的,即是未曾宣说;记住我已宣说的,即是已宣说。我未曾宣说的是什么?‘世界是永恒的’——我未曾宣说。‘世界非永恒的’——我未曾宣说。‘世界是有限的’——我未曾宣说。‘世界是无限的’——我未曾宣说。‘命与身是同一的’——我未曾宣说。‘命是一回事,身是另一回事’——我未曾宣说。‘如来 (Tathāgata) 死后存在’——我未曾宣说。‘如来死后不存在’——我未曾宣说。‘如来死后既存在又不存在’——我未曾宣说。‘如来死后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我未曾宣说。
8. “为什么我未曾宣说这些?因为它们没有利益,不属于梵行的基础,不能导向厌离、离欲、寂灭、寂静、亲证智、觉悟、涅槃。所以我未曾宣说。
9. “那么我已宣说的是什么?‘此是苦’——我已宣说。‘此是苦之集’——我已宣说。‘此是苦之灭’——我已宣说。‘此是导向苦灭之道’——我已宣说。
10. “为什么我已宣说这些?因为它们有利益,属于梵行的基础,能导向厌离、离欲、寂灭、寂静、亲证智、觉悟、涅槃。所以我已宣说。
“因此,摩罗迦子 (Māluṅkyāputta),记住我未曾宣说的,即是未曾宣说;记住我已宣说的,即是已宣说。”
这是世尊所说的话。尊者摩罗迦子 (Māluṅkyāputta) 对世尊的话感到满意和欢喜。2
(MN 63: Cūḷamāluṅkya Sutta; I 426–32)
(2)修行生活的心材
1.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王舍城 (Rājagaha) 的灵鹫山 (Vulture Peak);当时提婆达多 (Devadatta) 刚离开不久。3 在那里,世尊提到提婆达多,对比丘们如是说:
2. “诸比丘,于此,有善男子出于信,从家庭出家,过无家的生活,思惟:‘我遭受生、老、死,遭受愁、悲、苦、忧、恼;我遭受苦,为苦所困。这整堆苦的止息,必定是可以了知的。’他如此出家后,获得了利养、恭敬和名望。他因那利养、恭敬和名望而感到高兴,其意图得以满足。因此,他赞扬自己并贬低他人,说:‘我获得了利养和名望,但其他这些比丘却默默无闻、无足轻重。’他因那利养、恭敬和名望而陶醉,变得放逸,堕入放逸,由于放逸,他住在苦中。
“譬如有人需要心材,寻找心材,四处寻觅心材,来到一棵长有心材的大树前。他越过其心材、边材、内皮和外皮,砍下细枝与树叶,以为是心材而带走。那时,一个有好眼力的人看见他,可能会说:‘这位善人不知道心材、边材、内皮、外皮,或细枝与树叶。他需要心材,寻找心材,四处寻觅心材,来到一棵长有心材的大树前,却越过其心材、边材、内皮和外皮,砍下细枝与树叶,以为是心材而带走。无论这位善人要用心材做什么,他的目的都无法达成。’同样地,这位因那利养、恭敬和名望而陶醉的比丘也是如此。这位比丘被称为已取修行生活的细枝与树叶,并止步于此者。
3. “诸比丘,于此,有善男子出于信,从家庭出家,过无家的生活,思惟:‘我遭受生、老、死,遭受愁、悲、苦、忧、恼;我遭受苦,为苦所困。这整堆苦的止息,必定是可以了知的。’他如此出家后,获得了利养、恭敬和名望。他并未因那利养、恭敬和名望而感到高兴,其意图也未得以满足。他不会因此而赞扬自己并贬低他人。他不会因那利养、恭敬和名望而陶醉;他不会变得放逸而堕入放逸。由于精进,他成就了戒行。他因成就戒行而感到高兴,其意图得以满足。因此,他赞扬自己并贬低他人,说:‘我持戒,品行良好;但其他这些比丘不持戒,品行恶劣。’他因成就戒行而陶醉,变得放逸,堕入放逸,由于放逸,他住在苦中。
“譬如有人需要心材,寻找心材,四处寻觅心材,来到一棵长有心材的大树前。他越过其心材、边材和内皮,砍下其外皮,以为是心材而带走。那时,一个有好眼力的人看见他,可能会说:‘这位善人不知道心材……或细枝与树叶。他需要心材……却砍下其外皮,以为是心材而带走。无论这位善人要用心材做什么,他的目的都无法达成。’同样地,这位因成就戒行而陶醉的比丘也是如此。这位比丘被称为已取修行生活的外皮,并止步于此者。
4. “诸比丘,于此,有善男子出于信,从家庭出家,过无家的生活,思惟:‘我遭受生、老、死,遭受愁、悲、苦、忧、恼;我遭受苦,为苦所困。这整堆苦的止息,必定是可以了知的。’他如此出家后,获得了利养、恭敬和名望。他并未因那利养、恭敬和名望而感到高兴,其意图也未得以满足……。由于精进,他成就了戒行。他因成就戒行而感到高兴,但其意图并未得以满足。他不会因此而赞扬自己并贬低他人。他不会因成就戒行而陶醉;他不会变得放逸而堕入放逸。由于精进,他成就了定力。他因成就定力而感到高兴,其意图得以满足。因此,他赞扬自己并贬低他人,说:‘我已得定,心意专一;但其他这些比丘心散意乱。’他因成就定力而陶醉,变得放逸,堕入放逸,由于放逸,他住在苦中。
“譬如有人需要心材,寻找心材,四处寻觅心材,来到一棵长有心材的大树前。他越过其心材和边材,砍下其内皮,以为是心材而带走。那时,一个有好眼力的人看见他,可能会说:‘这位善人不知道心材……或细枝与树叶。他需要心材……却砍下其内皮,以为是心材而带走。无论这位善人要用心材做什么,他的目的都无法达成。’同样地,这位因成就定力而陶醉的比丘也是如此。这位比丘被称为已取修行生活的内皮,并止步于此者。
5. “诸比丘,于此,有善男子出于信,从家庭出家,过无家的生活,思惟:‘我遭受生、老、死,遭受愁、悲、苦、忧、恼;我遭受苦,为苦所困。这整堆苦的止息,必定是可以了知的。’他如此出家后,获得了利养、恭敬和名望。他并未因那利养、恭敬和名望而感到高兴,其意图也未得以满足……。由于精进,他成就了戒行。他因成就戒行而感到高兴,但其意图并未得以满足……。由于精进,他成就了定力。他因成就定力而感到高兴,但其意图并未得以满足。他不会因此而赞扬自己并贬低他人。他不会因成就定力而陶醉;他不会变得放逸而堕入放逸。由于精进,他成就了知见。4 他因那知见而感到高兴,其意图得以满足。因此,他赞扬自己并贬低他人,说:‘我活着能知能见,但其他这些比丘活着却无知无见。’他因那知见而陶醉,变得放逸,堕入放逸,由于放逸,他住在苦中。
“譬如有人需要心材,寻找心材,四处寻觅心材,来到一棵长有心材的大树前。他越过其心材,砍下其边材,以为是心材而带走。那时,一个有好眼力的人看见他,可能会说:‘这位善人不知道心材……或细枝与树叶。他需要心材……却砍下其边材,以为是心材而带走。无论这位善人要用心材做什么,他的目的都无法达成。’同样地,这位因那知见而陶醉的比丘也是如此。这位比丘被称为已取修行生活的边材,并止步于此者。
6. “诸比丘,于此,有善男子出于信,从家庭出家,过无家的生活,思惟:‘我遭受生、老、死,遭受愁、悲、苦、忧、恼;我遭受苦,为苦所困。这整堆苦的止息,必定是可以了知的。’他如此出家后,获得了利养、恭敬和名望。他并未因那利养、恭敬和名望而感到高兴,其意图也未得以满足……。当他精进时,他成就了戒行。他因成就戒行而感到高兴,但其意图并未得以满足……。当他精进时,他成就了定力。他因成就定力而感到高兴,但其意图并未得以满足……。当他精进时,他成就了知见。他因那知见而感到高兴,但其意图并未得以满足。他不会因此而赞扬自己并贬低他人。他不会因那知见而陶醉;他不会变得放逸而堕入放逸。由于精进,他证得永久的解脱。那位比丘不可能从那永久的解脱中退失。5
“譬如有人需要心材,寻找心材,四处寻觅心材,来到一棵长有心材的大树前,他只砍下其心材,知道那是心材而带走。那时,一个有好眼力的人看见他,可能会说:‘这位善人知道心材、边材、内皮、外皮,以及细枝与树叶。他需要心材,寻找心材,四处寻觅心材,来到一棵长有心材的大树前,他只砍下其心材,知道那是心材而带走。无论这位善人要用心材做什么,他的目的都能达成。’同样地,这位证得永久解脱的比丘也是如此。
7. “所以,诸比丘,这修行生活,其利益不是利养、恭敬和名望,其利益不是成就戒行,其利益不是成就定力,其利益也不是知见。而是这不动摇的心解脱,才是这修行生活的目标、心材和终极。’6
此为世尊所说。诸比丘心满意足,欢喜世尊所说。
(MN 29: Mahāsāropama Sutta; I 192–97)
(3)贪欲的消退
“诸比丘,若有其他宗派的游方者问你们:‘朋友们,在沙门乔达摩 (Gotama) 座下过梵行生活,是为了什么目的?’——被这样问时,你们应如此回答他们:‘朋友们,在世尊座下过梵行生活,是为了贪欲的消退。7’
“那么,诸比丘,若其他宗派的游方者问你们:‘可是,朋友们,是否有一条道路、一种方法,可以导向贪欲的消退?’——被这样问时,你们应如此回答他们:‘朋友们,有一条道路、一种方法,可以导向贪欲的消退。’
“诸比丘,那条道路、那种导向贪欲消退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这八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就是导向贪欲消退的道路、方法。
“诸比丘,被这样问时,你们应当如此回答那些其他宗派的游方者。
“[或者你们可以这样回答他们:]‘朋友们,在世尊座下过梵行生活,是为了断除诸结……为了根除随眠……为了遍知轮回的过程……为了灭尽诸漏……为了证得明与解脱之果……为了知见……为了无取着的究竟涅槃。’
“那么,诸比M丘,若其他宗派的游方者问你们:‘可是,朋友们,是否有一条道路、一种方法,可以达到无取着的究竟涅槃?’——被这样问时,你们应如此回答他们:‘朋友们,有一条道路、一种方法,可以达到无取着的究竟涅槃。’
“诸比丘,那条道路、那种达到无取着究竟涅槃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这八正道;即:正见……正定。这就是达到无取着究竟涅槃的道路、方法。
“诸比丘,被这样问时,你们应当如此回答那些其他宗派的游方者。”
(SN 45:41–48, combined; V 27–29)
第二篇:八正道分析
“诸比丘,我将为你们教导并分析八正道。仔细聆听,用心作意;我当宣说。”
“是的,尊者。”那些比丘回答道。世尊如此说道:
“诸比丘,什么是八正道呢?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诸比丘,什么是正见呢?了知苦,了知苦之集,了知苦之灭,了知导向苦灭之道:这称为正见。
“诸比丘,什么是正思惟呢?出离思惟、无恚思惟、无害思惟:这称为正思惟。
“诸比丘,什么是正语呢?远离妄语,远离离间语,远离粗恶语,远离无益语:这称为正语。
“诸比丘,什么是正业呢?远离杀生,远离不与取,远离邪淫:这称为正业。
“诸比丘,什么是正命呢?于此,圣弟子舍弃错误的谋生方式,以正当的方式谋生:这称为正命。
“诸比丘,什么是正精进呢?于此,诸比丘,比丘为了使未生的恶不善法不生起而生起意欲;他努力、发起精进、策励其心、奋斗。他为了断除已生的恶不善法而生起意欲……。他为了使未生的善法生起而生起意欲……。他为了使已生的善法持续、不衰、增长、广大、修习圆满而生起意欲;他努力、发起精进、策励其心、奋斗。这称为正精进。
“诸比丘,什么是正念呢?于此,诸比丘,比丘于身观身而住,热心、正知、具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欲和忧恼。他于受观受而住,热心、正知、具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欲和忧恼。他于心观心而住,热心、正知、具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欲和忧恼。他于法观法而住,热心、正知、具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欲和忧恼。这称为正念。
“诸比丘,什么是正定呢?于此,诸比丘,比丘远离诸欲,远离不善法,进入并安住于初禅那,此禅那有寻有伺,由远离而生喜乐。随着寻伺的平息,他进入并安住于第二禅那,此禅那有内在的自信与心的统一,无寻无伺,由定而生喜乐。随着喜的消退,他安住于舍,具念、正知,并以身感受乐;他进入并安住于第三禅那,圣者们称之为:‘他具舍、具念,安乐而住。’随着舍断乐与苦,以及先前喜与忧的消失,他进入并安住于第四禅那,此禅那不苦不乐,由舍而念清净。这称为正定。”
(SN 45:8; V 8–10)
第三篇:善友谊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释迦族中一个名为那伽罗卡 (Nāgaraka) 的城镇。那时,尊者阿难 (Ānanda) 走近世尊,顶礼后,坐于一旁,说道:
“尊者,此为梵行的一半,即:善友谊、善同伴、善同志。”8
“并非如此,阿难 (Ānanda)!并非如此,阿难!此为梵行的全部,阿难,即:善友谊、善同伴、善同志。当一位比丘有善友、善同伴、善同志时,可以预期他将培育和修习八正道。
“阿难,有善友、善同伴、善同志的比丘,如何培育和修习八正道呢?于此,阿难,比丘培育正见,其依止于远离、离欲、寂灭,成熟于解脱。他培育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其依止于远离、离欲、寂灭,成熟于解脱。阿难,有善友、善同伴、善同志的比丘,就是这样培育和修习八正道的。
“阿难,通过以下方法,也可以了知为何整个梵行就是善友谊、善同伴、善同志:阿难,通过依靠我这位善友,遭受生的众生得以从生中解脱;遭受老的众生得以从老中解脱;遭受死的众生得以从死中解脱;遭受愁、悲、苦、忧、恼的众生得以从愁、悲、苦、忧、恼中解脱。阿难,通过这个方法,可以了知为何整个梵行就是善友谊、善同伴、善同志。”
(SN 45:2; V 2–3)
第四篇:次第训练
1.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舍卫城 (Sāvatthī) 给孤独园 (Anāthapiṇḍika’s Park) 的祇树林 (Jeta’s Grove)。
2. 当时,婆罗门生闻 (Jāṇussoṇi) 在正午时分,驾着一辆由白母马拉的全白马车驶出舍卫城。他看见游方者毕洛帝卡 (Pilotika) 从远处走来,便问他:“婆蹉氏 (Vacchāyana),正午时分,您从何处而来?”9
“先生,我刚从沙门乔达摩 (Gotama) 那里来。”
“婆蹉氏 (Vacchāyana) 对沙门乔达摩智慧的明晰度有何看法?他是有智慧的,不是吗?”
“先生,我怎能了知沙门乔达摩智慧的明晰度呢?一个人肯定要与他同等,才能了知沙门乔达摩智慧的明晰度。”
“婆蹉氏 (Vacchāyana) 对沙门乔达摩的赞誉确实很高。” “先生,我怎能赞誉沙门乔达摩呢?沙门乔达摩为受赞誉者所赞誉,是天人中最优胜者。” “婆蹉氏 (Vacchāyana) 看到了什么理由,使他对沙门乔达摩有如此坚定的信心?”
3. “先生,譬如一位聪明的捕象师进入象林,在象林中看到一个又长又宽的大象足迹。他会得出结论:‘这真是一头巨大的公象。’同样地,当我看到沙门乔达摩的四个足迹时,我得出结论:‘世尊是正等觉者,法由世尊善说,僧团正行于善道。’是哪四个呢?
4. “先生,我曾在此见到某些博学的贵族,他们聪明、通晓他人的教义,如剖发般的弓箭手一样敏锐;他们四处游历,仿佛用他们敏锐的才智摧毁他人的见解。当他们听说:‘沙门乔达摩将要到访某某村庄或城镇,’他们便拟定一个问题:‘我们去找沙门乔达摩问这个问题。如果这样问他,他会这样回答,我们就能这样驳倒他的教义;如果那样问他,他会那样回答,我们就能那样驳倒他的教义。’“他们听说:‘沙门乔达摩已到访某某村庄或城镇。’他们去找沙门乔达摩,沙门乔达摩则以一场关于法的谈话来教导、敦促、激发和使他们欢喜。在被沙门乔达摩以关于法的谈话教导、敦促、激发和欢喜之后,他们甚至连问题都问不出口,又如何能驳倒他的教义呢?事实上,他们成了他的弟子。当我看到沙门乔达摩的这第一个足迹时,我得出结论:‘世尊是正等觉者,法由世尊善说,僧团正行于善道。’
5. “再者,我曾见到某些博学的婆罗门,他们聪明……。事实上,他们也成了他的弟子。当我看到沙门乔达摩的这第二个足迹时,我得出结论:‘世尊是正等觉者……。’
6. “再者,我曾见到某些博学的居士,他们聪明……。事实上,他们也成了他的弟子。当我看到沙门乔达摩的这第三个足迹时,我得出结论:‘世尊是正等觉者……。’
7. “再者,我曾见到某些博学的沙门,他们聪明……。他们甚至连问题都问不出口,又如何能驳倒他的教义呢?事实上,他们请求沙门乔达摩允许他们从家庭出家,过无家的生活,而他给予他们出家。出家后不久,他们独处、隐居、精进、热心、坚毅,通过亲证智,于现法中亲身证悟,进入并安住于那梵行的最高目标,善男子们正是为此目标而正确地从家庭出家,过无家的生活。他们这样说:‘我们差一点就迷失了,差一点就毁灭了,因为以前我们声称自己是沙门,却并非真正的沙门;我们声称自己是婆罗门,却并非真正的婆罗门;我们声称自己是阿罗汉,却并非真正的阿罗汉。但现在我们是沙门,现在我们是婆罗门,现在我们是阿罗汉了。’当我看到沙门乔达摩的这第四个足迹时,我得出结论:‘世尊是正等觉者……。’
“当我看到沙门乔达摩的这四个足迹时,我得出结论:‘世尊是正等觉者,法由世尊善说,僧团正行于善道。’”
8. 听完此言,婆罗门生闻 (Jāṇussoṇi) 从他那由白母马拉的全白马车上下来,将上衣搭在一肩上,向世尊的方向合掌致敬,并三次发出感叹:“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礼敬世尊、阿罗汉、正等觉者!或许什么时候我能见到乔达摩大师,与他交谈一番。”
9. 然后,婆罗门生闻 (Jāṇussoṇi) 去见世尊,并与他互致问候。当这段礼貌友好的交谈结束后,他坐于一旁,复述了他与游方者毕洛帝卡 (Pilotika) 的全部对话。于是世尊告诉他:“婆罗门,就此而言,象迹譬喻尚未详细讲完。至于如何详细讲完,请仔细聆听并用心作意我将要说的话。”——“好的,先生,”婆罗门生闻 (Jāṇussoṇi) 回答道。世尊如是说:
10. “婆罗门,譬如一位捕象师进入象林,在象林中看到一个又长又宽的大象足迹。一位聪明的捕象师还不会立刻得出结论:‘这真是一头巨大的公象。’为什么呢?在象林中,有些体型小的母象会留下大足迹,这可能是它们的足迹之一。他跟着足迹走,在象林中看到一个又长又宽的大象足迹,以及高处的刮痕。一位聪明的捕象师还不会立刻得出结论:‘这真是一头巨大的公象。’为什么呢?在象林中,有些高大的母象牙齿突出,会留下大足迹,这可能是它们的足迹之一。他继续跟着走,在象林中看到一个又长又宽的大象足迹,以及高处的刮痕和象牙的痕迹。一位聪明的捕象师还不会立刻得出结论:‘这真是一头巨大的公象。’为什么呢?在象林中,有些有象牙的高大母象会留下大足迹,这可能是它们的足迹之一。他继续跟着走,在象林中看到一个又长又宽的大象足迹,以及高处的刮痕、象牙的痕迹和折断的树枝。然后他看到那头公象在树根旁或空地上,或走动,或坐着,或躺着。他才得出结论:‘这才是那头巨大的公象。’
11. “同样地,婆罗门,于此,如来 (Tathāgata) 出现于世,是阿罗汉、正等觉者、明行具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他以亲证智证悟了这个世界,包括天人、魔罗 (Māra)、梵天 (Brahmā),这个有沙门和婆罗门、有天人和人类的群体后,将其昭示于众。他所教导的法,初善、中善、后善,义理和言辞俱佳;他揭示了一种完全圆满清净的梵行。
12. “一位居士或居士之子,或出生于其他家族者,听闻此法。听闻此法后,他对如来 (Tathāgata) 生起信心。怀着那份信心,他如此思惟:‘在家生活拥挤且充满尘垢;出家生活则空旷开阔。住在家里,要过一种像磨亮的贝壳一样完全圆满清净的梵行生活,实属不易。不如我剃除须发,穿上袈裟,从家庭出家,过无家的生活。’日后,他舍弃或多或少的财富,舍弃或大或小的亲属圈,剃除须发,穿上袈裟,从家庭出家,过无家的生活。
13. “如此出家并具备比丘的学处和生活方式后,他舍弃杀生,戒绝杀生;放下棍棒与武器,具足惭愧,仁慈,对一切众生怀有慈悲心而住。舍弃不与取,他戒绝不与取;只取所予,只望所予,他不偷盗,清净而住。舍弃性关系,他修持梵行,独身而住,远离淫欲的粗劣行为。
“他舍弃妄语,远离妄语;他说真实语,信守真理,值得信赖且可靠,是不欺骗世人的人。他舍弃两舌,远离两舌;他在此处听闻后,不到别处去说,以离间那些人,也不将别处听闻的告诉这些人,以离间这些人;因此,他是分裂者的调解者,友谊的促进者,喜爱和合,乐于和合,欢喜和合,说促进和合的话语。他舍弃恶口,远离恶口;他说的话语柔和,悦耳,可爱,能入人心,有礼,为众人所喜爱,为众人所接受。他舍弃绮语,远离绮语;他适时而语,说事实,说善事,说佛法与戒律;他在适当的时候说出值得记取、合理、适度且有益的话语。
“他远离损害种子和植物。他一日一食,远离非时食。10他远离观看舞蹈、歌唱、音乐和不适宜的表演。他远离佩戴花环、涂抹香水和以膏油美饰。他远离高广大床。他远离接受金银。他远离接受生谷。他远离接受生肉。他远离接受妇女和女孩。他远离接受男女奴隶。他远离接受山羊和绵羊。他远离接受家禽和猪。他远离接受大象、牛、马和母马。他远离接受田地和土地。他远离为人差使和传递信息。他远离买卖。他远离使用不实的秤、不实的金属和不实的量器。他远离接受贿赂、欺骗、诈骗和诡计。他远离伤害、谋杀、捆绑、抢劫、掠夺和暴力。
14. “他满足于足以保护身体的衣物和足以维持肚腹的饮食,无论去哪里,他都只带着这些东西出发。就像一只鸟,无论飞到哪里,都只以双翼为唯一的负担;同样地,比丘满足于足以保护身体的衣物和足以维持肚腹的饮食,无论去哪里,他都只带着这些东西出发。拥有这圣戒蕴,他在内心中体验到无过之乐。
15. “以眼见色时,他不取相,不取随相。11因为如果他放任眼根不加守护,贪欲和忧恼等邪恶不善法就可能侵入他,所以他修习防护之道,守护眼根,致力于防护眼根。以耳闻声时……以鼻嗅香时……以舌尝味时……以身触物时……以意知法时,他不取相,不取随相。因为如果他放任意根不加守护,贪欲和忧恼等邪恶不善法就可能侵入他,所以他修习防护之道,守护意根,致力于防护意根。拥有这圣根律仪,他在内心中体验到无染之乐。
16. “他在前进和返回时,保持正知而行;在向前看和向旁看时,保持正知而行;在屈伸肢体时,保持正知而行;在穿着衣袍和携带外衣与钵时,保持正知而行;在饮食、咀嚼和品尝时,保持正知而行;在大小便时,保持正知而行;在行走、站立、坐着、入睡、醒来、说话和保持沉默时,保持正知而行。
17. “拥有这圣戒蕴,这圣根律仪,以及这圣念与正知,他去到一处僻静的住所:森林、树下、山中、峡谷、山洞、墓地、丛林、空地、草堆。
18. “他托钵回来,饭后,便结跏趺坐,保持身体正直,将念安立于面前。舍弃对世间的贪欲,他以离贪欲之心安住;他净化自心,远离贪欲。12舍弃瞋恚,他以无瞋恚之心安住,慈悲一切众生的福祉;他净化自心,远离瞋恚。舍弃昏沉睡眠,他远离昏沉睡眠而住,觉知光明,具念正知;他净化自心,远离昏沉睡眠。舍弃掉举追悔,他远离散乱而住,内心平静;他净化自心,远离掉举追悔。舍弃疑惑,他超越疑惑而住,对善法不再困惑;他净化自心,远离疑惑。
19. “如此舍弃这五盖——削弱智慧的心之杂染后,远离欲乐,远离不善法,他进入并安住于初禅,有寻有伺,具足离生喜乐。婆罗门,这被称为如来的足迹,如来所刮擦的痕迹,如来所标记的印记,但圣弟子尚不作此结论:‘世尊是圆满觉悟者,法是世尊善说的,僧团是善行道的。’13
20. “再者,随着寻与伺的平息,他进入并安住于二禅,此禅内心安信,心一境性,无寻无伺,具足定生喜乐。婆罗门,这也称为如来的足迹……但圣弟子尚不作此结论:‘世尊是圆满觉悟者……’
21. “再者,随着喜的消退,他住于舍,具念正知,以身感受乐;他进入并安住于三禅,圣者们宣称此禅为:‘他是舍、念、乐住者。’婆罗门,这也称为如来的足迹……但圣弟子尚不作此结论:‘世尊是圆满觉悟者……’
22. “再者,随着舍弃乐与苦,以及先前喜与忧的消失,他进入并安住于四禅,此禅不苦不乐,因舍而念清净。婆罗门,这也称为如来的足迹……但圣弟子尚不作此结论:‘世尊是圆满觉悟者……’
23.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净、明亮、无瑕、离诸杂染、柔软、适业、稳固且达到不动时,他将心导向宿命通智。他忆起自己种种过去生,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一百生、一千生、十万生,许多世界成劫,许多世界坏劫,许多世界成坏劫:‘在那里,我叫某某名,属某某族,有某某相貌,吃某某食物,经历某某苦乐,寿命多长;从那里死去后,我重生于别处;在那里,我也叫某某名,属某某族,有某某相貌,吃某某食物,经历某某苦乐,寿命多长;从那里死去后,我重生于此。’如此,他忆起自己种种过去生的情状与细节。婆罗门,这也称为如来的足迹……但圣弟子尚不作此结论:‘世尊是圆满觉悟者……’
24.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净、明亮、无瑕、离诸杂染、柔软、适业、稳固且达到不动时,他将心导向众生生死通智。他以清净超凡的天眼,看见众生的死亡与再生,劣者与胜者,美者与丑者,幸运者与不幸者。他了知众生如何随其业而流转:‘这些众生,身、语、意行为不善,毁谤圣者,持错误见解,并依错误见解行事,身坏命终后,已重生于苦界、恶趣、堕处、地狱;但那些众生,身、语、意行为良善,不毁谤圣者,持正确见解,并依正确见解行事,身坏命终后,已重生于善趣、天界。’如此,他以清净超凡的天眼,看见众生的死亡与再生,劣者与胜者,美者与丑者,幸运者与不幸者,并了知众生如何随其业而流转。婆罗门,这也称为如来的足迹……但圣弟子尚不作此结论:‘世尊是圆满觉悟者……’
25.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净、明亮、无瑕、离诸杂染、柔软、适业、稳固且达到不动时,他将心导向漏尽通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这是苦的起源。这是苦的止息。这是导向苦止息之道。’他如实了知:‘这是诸漏。这是诸漏的起源。这是诸漏的止息。这是导向诸漏止息之道。’ “婆罗门,这也称为如来的足迹,如来所刮擦的痕迹,如来所标记的印记,但圣弟子仍未作此结论:‘世尊是圆满觉悟者,法是世尊善说的,僧团是善行道的。’相反,他正在趋向此结论的过程中。14
26. “当他如此知、如此见时,他的心从欲漏、有漏、无明漏中解脱出来。当解脱时,智生起:‘已解脱。’他了知:‘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婆罗门,这也称为如来的足迹,如来所刮擦的痕迹,如来所标记的印记。正是在这一点上,圣弟子得出了结论:‘世尊是圆满觉悟者,法是世尊善说的,
僧团是善行道的。’15婆罗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象足迹的比喻才被完整详尽地阐述了。”
27. 此话说完,婆罗门生闻(Jāṇussoṇi)对世尊说:“善哉,乔达摩(Gotama)尊者!善哉,乔达摩尊者!乔达摩尊者以多种方式阐明了法,犹如扶正已倒之物,揭示隐藏之物,为迷途者指明道路,或在黑暗中举灯,使有眼者能见色。我今皈依乔达摩尊者,皈依法,皈依比丘僧团。愿乔达摩尊者接受我为居士,从今日起,直至生命终结,皆皈依于此。”
(MN 27: 《小象足迹喻经》; I 175–84)
第五篇:更高阶段训练的比喻
12. “诸比丘,于此,有比丘去到一处僻静的住所:森林、树下、山中、峡谷、山洞、墓地、丛林、空地、草堆。
13. “他托钵回来,饭后,便结跏趺坐,保持身体正直,将念安立于面前。舍弃对世间的贪欲……[如前文 §18]……他净化自心,远离疑惑。
14. “诸比丘,譬如一人借贷经商,生意成功,得以偿还所有旧债,且尚有余钱可养活妻子;念及于此,他会感到高兴和充满喜悦。又譬如一人患病,痛苦不堪,病情严重,饮食不进,身体无力,但后来他从病中康复,饮食合宜,身体恢复力量;念及于此,他会感到高兴和充满喜悦。又譬如一人身陷囹圄,但后来获释,安全无虞,财产无损;念及于此,他会感到高兴和充满喜悦。又譬如一人为奴,不能自主,依附于人,想去何处都不得,但后来他从奴役中解脱,得以自主,不依附于人,成为自由人,想去何处便可去;念及于此,他会感到高兴和充满喜悦。又譬如一人携财富财产,进入穿越沙漠之路,但后来他穿越沙漠,安全无虞,财产无损;念及于此,他会感到高兴和充满喜悦。同样地,诸比丘,当这五盖尚未在自身中舍弃时,比丘视它们分别如债务、疾病、监狱、奴役和穿越沙漠之路。但当这五盖已在自身中舍弃时,他视之为脱离债务、病愈、出狱、脱离奴役和安全之地。
15. “舍弃这五盖——削弱智慧的心之杂染后,远离欲乐,远离不善法,他进入并安住于初禅,有寻有伺,具足离生喜乐。他让这离生喜乐浸透、湿润、充满、遍布此身,以至于他全身无处不被这离生喜乐所遍布。就像一个熟练的澡堂师傅或其学徒,将沐浴粉堆在金属盆中,逐渐洒水揉捏,直到水湿润他的沐浴粉球,使其浸透,内外皆遍,而粉球本身却不渗漏;同样地,比丘让这离生喜乐浸透、湿润、充满、遍布此身,以至于他全身无处不被这离生喜乐所遍布。
16. “再者,诸比丘,随着寻与伺的平息,他进入并安住于二禅,此禅内心安信,心一境性,无寻无伺,具足定生喜乐。他让这定生喜乐浸透、湿润、充满、遍布此身,以至于他全身无处不被这定生喜乐所遍布。譬如有一湖,其水从下涌出,无东西南北之流入,亦不时有雨水补充,于是湖中涌出的清凉泉水,使清凉之水浸透、湿润、充满、遍布全湖,以至于全湖无处不被清凉之水所遍布;同样地,比丘让这定生喜乐浸透、湿润、充满、遍布此身,以至于他全身无处不被这定生喜乐所遍布。
17. “再者,诸比丘,随着喜的消退,他住于舍,具念正知,以身感受乐;他进入并安住于三禅,圣者们宣称此禅为:‘他是舍、念、乐住者。’他让这离喜之乐浸透、湿润、充满、遍布此身,以至于他全身无处不被这离喜之乐所遍布。譬如在青莲、红莲或白莲池中,有些莲花生于水中,长于水中,浸于水中而不升出水面,清凉之水浸透、湿润、充满、遍布它们,直至顶端与根部,以至于所有莲花无处不被清凉之水所遍布;同样地,比丘让这离喜之乐浸透、湿润、充满、遍布此身,以至于他全身无处不被这离喜之乐所遍布。
18. “再者,诸比丘,随着舍弃乐与苦,以及先前喜与忧的消失,比丘进入并安住于四禅,此禅不苦不乐,因舍而念清净。他坐着,让纯净明亮的心遍布此身,以至于他全身无处不被纯净明亮的心所遍布。譬如一人从头到脚盖着白布而坐,以至于他全身无处不被白布所遍布;同样地,比丘坐着,让纯净明亮的心遍布此身,以至于他全身无处不被纯净明亮的心所遍布。
19.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净、明亮、无瑕、离诸杂染、柔软、适业、稳固且达到不动时,他将心导向宿命通智。他忆起自己种种过去生,即一生、二生……[如前文 §23]……如此,他忆起自己种种过去生的情状与细节。譬如一人从自己的村庄到另一村庄,然后再回到自己的村庄,他可能会想:‘我从自己的村庄到那个村庄,在那里我如此站立,如此坐着,如此说话,如此沉默;又从那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在那里我如此站立,如此坐着,如此说话,如此沉默;又从那个村庄回到自己的村庄。’同样地,比丘忆起自己种种过去生……如此,他忆起自己种种过去生的情状与细节。
20.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净、明亮、无瑕、离诸杂染、柔软、适业、稳固且达到不动时,他将心导向众生生死通智……[如前文 §24]……如此,他以清净超凡的天眼,看见众生的死亡与再生,劣者与胜者,美者与丑者,幸运者与不幸者,并了知众生如何随其业而流转。譬如,有两座有门的房子,一个视力好的人站在两房之间,看到人们进出房屋,来来往往,同样地,比丘以清净超凡的天眼,看见众生的死亡与再生……并了知众生如何随其业而流转。
21. “当他的心如此得定、清净、明亮、无瑕、离诸杂染、柔软、适业、稳固且达到不动时,他将心导向漏尽通智。他如实了知:‘这是苦’……[如前文 §§25–26]……他了知:‘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譬如在山坳中有一湖,清澈、明净、宁静,一个视力好的人站在岸边,能看见贝壳、砂砾和卵石,也能看见鱼群游动和停歇,他可能会想:‘这是这个湖,清澈、明净、宁静,这里有这些贝壳、砂砾和卵石,还有这些鱼群在游动和停歇。’同样地,比丘如实了知:‘这是苦。’……他了知:‘生死已尽,圣洁的生活已经圆满,所应做之事皆已完成,不再有任何形式的后有。’”
(摘自 MN 39: 《大马邑经》; I 274–80)
注释
-
在这十种见解中,那些持有关于世界 (loka) 观念的见解,也暗含着对自我 (attā) 的类似观念。因此,第一对是常见和断见的对立。灵魂与身体相同的观点是唯物主义,是一种断见;灵魂与身体不同的观点是常见。认为如来 (Tathāgata)——一个解脱者——死后存在的观点是常见;认为他死后不存在的观点是断见。认为他既存在又不存在的观点是一种结合了常见和断见特征的折衷学说;认为他既非存在亦非不存在的观点是怀疑主义或不可知论,它否认我们能确定他死后的状况。所有这些观点,从佛教的角度来看,都预设了如来目前作为一个自我而存在。因此,它们都始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区别仅在于它们以不同的方式设定了自我的命运。 ↩
-
那些一直想知道那位差点为了满足其形而上学好奇心而离开佛陀的比丘的命运的人,当知道摩罗迦子 (Māluṅkyāputta) 在晚年接受了佛陀关于六根的简短开示,进入独处,并证得阿罗汉果时,应该会感到欣慰。见 SN 35:95。 ↩
-
提婆达多 (Devadatta) 是佛陀野心勃勃的堂兄弟,他企图杀死佛陀并篡夺僧团 (Saṅgha) 的控制权。当这些企图失败后,他分裂出去,试图建立自己的教派并自任领袖。见髻智长老 (Ñāṇamoli) 所著《佛陀的一生》(Life of the Buddha),第266–69页。 ↩
-
Ps:“知见” (ñāṇadassana) 此处指天眼通,即能看见普通视觉无法看见的微细色法。 ↩
-
此译文遵循 Be 版和 Ce 版,在前一句中为 asamayavimokkhaṃ,在本句中为 asamayavimuttiyā。Ee 版似乎错误地将这两个复合词读为 samaya,并将 ṭhānaṃ 读为 aṭṭhānaṃ。Ps 引用《无碍解道》(Paṭisambhidāmagga) 对 asamayavimokkha(字面意为非时或“恒时”解脱)的定义为四道、四果和涅槃 (Nibbāna),对 samayavimokkha(时解脱)的定义为四禅那 (jhānas) 和四无色定。另见 MN 122.4。 ↩
-
Ps 说,“不动心解脱” (akuppā cetovimutti) 是阿罗汉果。因此,“恒时解脱”——因其包含所有四道四果——其范围比“不动心解脱”更广。唯有后者被宣称为梵行的目标。 ↩
-
Rāgavīrāgatthaṃ。 这也可以有些别扭地译为“为了对贪欲的离染”,或“为了对欲念的离欲”。 ↩
-
Spk:当阿难 (Ānanda) 独处时,他想:“比丘的修行,依赖善友和自身的精进努力才能成功;因此一半依赖善友,一半依赖自身的精进努力。” ↩
-
婆车亚那是毕洛帝迦 (Pilotika) 的族姓。 ↩
-
见第436页(第五章,注19)。 ↩
-
相 (nimitta) 是所缘的显著特征,当不具正念地执取时,会引发染污的念头;随相 (anubyañjana) 是当一个人不防护诸根时,吸引其注意力的细节。“贪与忧” (abhijjhā-domanassa) 意味着对感官对象产生的欲望和厌恶、吸引和排斥这两种对立的反应。 ↩
-
此处,贪 (abhijjhā) 与欲欲 (kāmacchanda) 同义,即五盖中的第一个。这整段都在讨论如何克服五盖。 ↩
-
他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禅那 (jhānas) 以及接下来的前两种神通,并非佛陀教法所独有。 ↩
-
根据 Ps 的说法,这显示了出世间道的时机。因为在这一点上,圣弟子尚未完成他的任务,所以他对三宝尚未得出结论 (na tveva niṭṭhaṃ gato hoti);相反,他正在得出结论的过程中 (niṭṭhaṃ gacchati)。经文以一种在英语和巴利语中同样可行的方式,双关了“得出结论”这一表达的含义。 ↩
-
Ps:这显示了弟子证得阿罗汉果,完全完成了他的任务,并对三宝得出了结论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