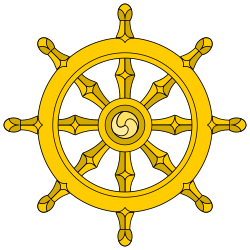Index
第一章:人类的处境

导言
与其他宗教教义一样,佛陀的教法源于对人类境况核心中各种紧张状态的回应。他的教法与其他宗教处理人类境况的方法不同之处在于,他审视这些紧张状态的直接性、彻底性和不妥协的现实主义。佛陀不提供治标不治本的姑息疗法,让潜在的病根潜伏在表面之下;相反,他将我们的生存之疾追溯到其最根本、如此顽固和破坏性的原因,并向我们展示如何将这些原因彻底根除。然而,虽然佛法最终将引向根除苦因的智慧,但它并非从那里开始,而是从观察日常经验中严酷的事实开始。在这里,它的直接性、彻底性和强硬的现实主义同样显而易见。教法始于要求我们培育一种名为“如理作意”(yoniso manasikāra)的能力,即审慎的作意。佛陀要求我们停止浑浑噩噩地度日,转而审慎地注意那些随处可见、亟需我们持续审思的简单真理。
在这些真理中,最显而易见且不可避免的一个,同时也是我们最难完全承认的一个,即我们注定会衰老、生病和死亡。人们普遍认为,佛陀引导我们认识老与死的实相,是为了激励我们走上通往涅槃(Nibbāna)的出离之道,即从生死轮回中完全解脱。然而,虽然这可能是他的最终意图,但这并非当我们向他寻求指引时,他希望在我们心中唤起的首要回应。佛陀意图在我们心中唤起的初步回应是道德层面上的。通过提请我们注意我们受缚于老与死的状况,他试图在我们心中激发一种坚定的决心,即远离不善的生活方式,转而采纳善的替代方式。
再者,佛陀最初的道德诉求,不仅建立在对其他众生的慈悲情感之上,也建立在我们对自己长远福祉和快乐的本能关怀之上。他试图让我们看到,遵循道德准则行事,将使我们能够确保自己当前和长远的福祉。他的论证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前提:行为会带来后果。如果我们想改变我们习惯的方式,就必须确信这一原则的有效性。具体来说,要从一种自我僵化的生活方式转变为一种真正富有成效且内心充实的方式,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行为对我们自身有后果,这些后果可能在今生和来生回向到我们自己身上。
构成本章第一篇的三篇经文,各自以其方式雄辩地确立了这一点。第一章第一篇(1)阐明了所有已投生的众生都必须经历老与死的必然法则。虽然这篇经文乍看之下似乎只是在陈述一个自然事实,但通过引用社会上层阶级(富有的统治者、婆罗门和居家者)以及解脱的阿罗汉为例,它在言辞中融入了微妙的道德讯息。第一章第一篇(2)以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山喻更明确地揭示了这一讯息,它深刻地揭示了当“老与死正向我们滚滚而来”时,我们的人生任务是过正直的生活,行善积德。关于“天使”的经文——第一章第一篇(3)——则确立了其推论:当我们未能认识到身边的“天使”,当我们错过了老、病、死这些隐藏的警示信号时,我们就会变得放逸和行为鲁莽,造下不善业,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
认识到我们注定会衰老和死亡,打破了欲乐、财富和权力对我们施加的迷恋魔咒。它驱散了困惑的迷雾,并激励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或许还没准备好放弃家庭和财产,去过一种无家游方和独处禅修的生活,但这并非佛陀通常期望于其在家弟子的选择。相反,如我们上文所见,他从我们的生命终将老死这一事实中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是与业和再生的双重法则交织在一起的道德教训。业的法则规定,我们的不善与善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了今生:不善的行为导致再生于苦界,并带来未来的痛苦;善的行为则导致善趣再生,并带来未来的福祉和快乐。既然我们必须衰老和死亡,我们就应该时刻意识到,我们目前可能享有的任何繁荣都只是暂时的。我们只有在年轻健康时才能享受它;而当我们死亡时,我们新造的业将有机会成熟并产生其自身的果报。届时我们必须收获我们行为应得的果报。为了我们的长远未来福祉,我们应审慎地避免导致痛苦的恶行,并精进地行持能在今生和来生带来快乐的善业。
在第二篇中,我们探讨了人类生活的三个方面,我将其归纳在“未经反思的生活之苦”这一标题下。这些类型的苦,与老、死相关的苦在一个重要方面有所不同。老和死与肉身存在紧密相连,因此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对于凡夫还是解脱的阿罗汉都是如此——本章第一篇的文本已说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本篇收录的三篇文本都区分了凡夫,即“未受教导的凡夫”(assutavā puthujjana),与佛陀的智慧追随者,即“受过教导的圣弟子”(sutavā ariyasāvaka)。
这些区别中的第一个,在第一章第二篇(1)中有所阐述,围绕着对苦受的反应。凡夫和圣弟子都会经历身体的苦受,但他们对这些感受的反应不同。凡夫以厌恶之心回应,因此,在身体的苦受之上,还会经历心的苦受:忧、怨或苦恼。圣弟子在遭受身苦时,会耐心地忍受这种感受,没有忧、怨或苦恼。人们普遍认为身苦和心苦密不可分,但佛陀在两者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他认为,虽然肉身存在不可避免地与身苦相连,但这种痛苦不一定会触发我们习惯性回应的忧、惧、怨、恼等情绪反应。通过心的训练,我们可以培育出必要的念与正知,以勇气、耐心和舍心来忍受身苦。通过观智,我们可以开发足够的智慧,以克服对苦受的恐惧,以及在令人分心的感官纵情中寻求慰藉的需求。
人类生活的另一个方面,凸显了凡夫与圣弟子之间的差异,那就是命运的变迁。佛教典籍巧妙地将其归结为四对对立面,称为八世间法(aṭṭha lokadhammā):得与失、誉与毁、称与讥、乐与苦。第一章第二篇(2)展示了凡夫和圣弟子在应对这些变化时的不同反应。凡夫因成功获得得、誉、称、乐而兴高采烈,当面临其不欲的对立面时则意志消沉,而圣弟子则保持不为所动。通过将无常的理解应用于顺境和逆境,圣弟子能够安住于舍,不执着于顺境,不排斥逆境。这样的弟子舍弃爱憎、忧恼,并最终赢得最高的祝福:从苦中完全解脱。
第一章第二篇(3)在一个更根本的层面上审视了凡夫的困境。因为错误地认知事物,凡夫会因变化而烦乱,尤其是当这种变化影响到他们自身的身体和心时。佛陀将身心的组成部分分为五类,称为“五取蕴”(pañc’upādānakkhandhā):色、受、想、行、识(详情见第305–07页)。这五蕴是我们通常用来构建个人认同感的基石;它们是我们执取为“我的”、“我”和“我的自我”的事物。我们所认同的任何事物,我们视为自我或自我所属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归入这五蕴之中。因此,五蕴是“认同”与“占有”的最终依据,这是我们建立自我感的两个基本活动。由于我们在自我和个人身份的观念中投入了强烈的情感关注,当它们所依附的对象——五蕴——经历变化时,我们自然会感到焦虑和苦恼。在我们的认知中,经历变化的不仅仅是无我的现象,而是我们自身的身份,我们所珍视的自我,而这正是我们最恐惧的。然而,如本经文所示,一位圣弟子已经以智慧清晰地洞见了所有恒常自我观念的虚妄本质,因此不再认同五蕴。因此,圣弟子能够无忧无虑地面对它们的变化,面对它们的变异、衰败和毁灭时,心不扰动。
烦扰和动乱不仅在个人和私密层面上折磨着人类生活,也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互动中。自古以来,我们的世界一直充满着暴力冲突与对抗。名称、地点和毁灭的工具可能会改变,但其背后的力量、动机、贪与嗔的表现却相当恒定。《尼柯耶》证明,佛陀深刻地意识到了人类境况的这一维度。尽管他的教法,以其对道德自律和心的培育的强调,主要旨在实现个人的觉悟与解脱,但佛陀也试图为人们提供一个庇护所,以逃离残酷折磨人类生活的暴力和不公。这在他对慈与悲的强调中显而易见;在行为无害、言语柔和上;以及在和平解决争端上。
本章的第三篇包含四篇简短的文本,探讨暴力冲突与不公的根本原因。从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并不只是呼吁改变社会的外部结构。他证明了这些黑暗现象是人心不善倾向的外部投射,因此指出了内在的改变是建立和平与社会正义的并行条件。本篇收录的四篇文本,每一篇都将冲突、暴力、政治压迫和经济不公追溯其因;每一篇都以其自己的方式将这些原因定位在心中。
第一章第三篇(1)解释了在家众之间的冲突源于对欲乐的执取,而出家修行者之间的冲突则源于对见解的执取。第一章第三篇(2)是佛陀与萨kka(Sakka)——前佛教时期印度的天人(devas)之主——之间的一段对话,将仇恨与敌意追溯至嫉妒与悭吝;佛陀又从那里将它们追溯至影响我们觉知与认知过程处理感官所提供信息的根本扭曲。第一章第三篇(3)提供了著名的缘起链的另一个版本,它从受进展到爱,再从爱经由其他缘而导致“拿起棍棒与武器”以及其他类型的暴力行为。第一章第三篇(4)描绘了三不善根——贪、嗔、痴——如何对整个社会造成可怕的反响,引发暴力、权力欲和不公正地施加痛苦。所有四篇文本都意味着,任何对社会意义重大且持久的变革,都需要个体道德品质的显著改变;因为只要贪、嗔、痴作为行为的决定因素而横行,其后果必然是持续有害的。
佛陀的教法探讨了人类境况的第四个方面,这与我们迄今为止考察的三个方面不同,它并非我们能直接感知的。这就是我们对生死轮回的束缚。从本章最后一篇所选的文本中,我们看到佛陀教导说,我们的个体生命仅仅是一系列再生中的一个阶段,这一系列再生一直在进行,没有任何可辨识的时间起点。这一系列的再生被称为轮回(saṃsāra),这个巴利语词暗示了无方向漂泊之意。无论我们想在时间上回溯多远去寻找宇宙的开端,我们永远找不到一个最初的创造时刻。无论我们想追溯任何一个特定的生命序列有多远,我们永远无法达到一个最初的起点。根据第一章第四篇(1)和I,4(2),即使我们跨越世界系统去追溯我们父母的序列,我们也只会发现更多的父母,一直回溯到遥远的天际。
此外,这个过程不仅是无始的,也可能是无终的。只要无明和渴爱依然存在,这个过程就会无限期地延续到未来,看不到尽头。对于佛陀和早期佛法而言,这首先是人类处境核心的决定性危机:我们被束缚在生死轮回的锁链上,而束缚我们的正是我们自身的无明和渴爱。在saṃsāra中毫无意义的流浪,是在一个广阔得不可思议的宇宙背景下发生的。一个世界系统从形成、发展到鼎盛、收缩乃至崩坏所经历的时间,被称为一kappa(梵语:kalpa),即一劫。第一章第四篇(3)用一个生动的譬喻来暗示一劫的时间长度;第一章第四篇(4)用另一个生动的譬喻来说明我们已经流浪了无数劫。
当众生在黑暗的笼罩下,从一生到另一生地流浪时,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坠入生、老、病、死的深渊。但由于他们的渴爱驱使着他们不断地追求满足,他们很少停下来,退后一步,仔细审视自己的生存困境。正如第一章第四篇(5)所说,他们只是围绕着“五蕴”不停地旋转,就像一只被拴住的狗绕着柱子打转一样。由于无明使他们无法认识到自己处境的恶劣本质,他们甚至无法辨别通往解脱的道路踪迹。大多数众生沉浸在感官之乐的享受中。另一些人则被对权力、地位和尊重的需求所驱使,徒劳地试图填补永不满足的渴望,虚度一生。许多人因害怕死亡时的断灭,便构建了种种信仰体系,将永生的前景赋予他们个体的自我,即他们的灵魂。少数人渴望一条解脱之道,却不知何处去寻。佛陀正是为了提供这样一条道路,才出现在我们中间。
第一篇:老、病、死
(1)老与死
在舍卫城(Sāvatthī),拘萨罗国(Kosala)的波斯匿王(Pasenadi)对世尊说:“尊者,可有任何生者能免于老死吗?”1
“大王,没有任何生者能免于老死。即使是那些富裕的刹帝利(khattiyas)——富有,拥有巨大的财富和财产,拥有丰富的金银,丰富的珍宝和商品,丰富的财富和谷物——因为他们已经出生,所以也无法免于老死。即使是那些富裕的婆罗门……富裕的居士——富有……拥有丰富的财富和谷物——因为他们已经出生,所以也无法免于老死。即使是那些已证阿罗汉的比丘,他们的诸漏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已舍重担,已证己利,彻底摧毁了有结,通过究竟智而完全解脱:即使对他们而言,此身也终将败坏,终将放下。”2
“君王华丽的马车会朽坏,
此身也同样会衰败。
但善人之法永不衰败:
善人与善人如是说。”
(SN 3:3; I 71 <163–64>)
(2)大山譬喻
在舍卫城(Sāvatthī),一日中午,拘萨罗国(Kosala)的波斯匿王(Pasenadi)前来拜见世尊,顶礼后,坐于一旁。世尊于是问他:“大王,现在正值中午,您从何处来?”
“尊者,我刚才正在处理那些典型的王室事务,君王们沉醉于权力的迷醉,沉迷于对感官之乐的贪欲,在自己的国家获得了稳固的统治,并征服了广大的领土进行统治。”
“大王,您认为如何?假设有一个人从东方来,他值得信赖且可靠,他对您说:‘大王,您确实应该知道:我从东方来,在那里我看到一座如云般高耸的大山正向这边移来,碾压一切众生。大王,请做您认为该做的事吧。’然后第二个人从西方来……第三个人从北方来……第四个人从南方来,他值得信赖且可靠,他对您说:‘大王,您确实应该知道:我从南方来,在那里我看到一座如云般高耸的大山正向这边移来,碾压一切众生。大王,请做您认为该做的事吧。’大王,如果出现如此巨大的危难,如此可怕的人命毁灭,而人身又如此难得,应当做些什么呢?”
“尊者,如果出现如此巨大的危难,如此可怕的人命毁灭,而人身又如此难得,除了依法而活,行持正义,造作善业与功德之事,还能做些什么呢?”
“大王,我告知您,我向您宣告:老与死正向您逼近。大王,当老与死正向您逼近时,应当做些什么呢?”
“尊者,当老与死正向我逼近时,除了依法而活,行持正义,造作善业与功德之事,还能做些什么呢?
“尊者,君王们沉醉于权力的迷醉,沉迷于对感官之乐的贪欲,在自己的国家获得了稳固的统治,并征服了广大的领土,他们通过象兵战、马兵战、车兵战和步兵战来征服;但当老与死逼近时,这些战斗毫无取胜的希望,没有成功的可能。尊者,在这王庭中,有谋臣能在敌人到来时,用计谋分化他们;但当老与死逼近时,用计谋毫无取胜的希望,没有成功的可能。尊者,在这王庭中,库房里储存着大量的金银,我们能用这些财富来安抚来犯的敌人;但当老与死逼近时,用财富毫无取胜的希望,没有成功的可能。尊者,当老与死正向我逼近时,除了依法而活,行持正义,造作善业与功德之事,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正是如此,大王!正是如此,大王!当老与死正向您逼近时,除了依法而活,行持正义,造作善业与功德之事,您还能做些什么呢?”
此为世尊所说。说完这些,善逝、导师又进一步说道:“犹如坚固的岩石山,
巨大,高耸入云,
或从四面八方合拢,
碾碎四方的一切——
老与死也是如此,
降临于众生之上——
“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
贱民与清道夫:
它们沿途无一幸免,
碾碎一切。
“象兵、车兵、步兵,
皆无取胜希望。
无法用计谋战胜它们,
也无法用财富收买它们。
“因此,有智慧的人,
为自身利益着想,
应坚定地建立信心,
于佛、法、僧之中。
“若人以身、语、意,
奉法而行,
则于今生受人赞誉,
死后亦喜生天界。”(SN 3:25; I 100–102 <224–29>)
(3)天的使者
“比丘们,有三位天的使者。3是哪三位?
“有一个人在身、语、意方面行为不善。身体分解,死后,他重生于苦处、恶趣、堕处、地狱。那里的地狱狱卒抓住他的双臂,将他带到死神阎魔(Yama)面前,4说:‘陛下,此人既不尊敬父母,也不尊敬沙门和婆罗门,亦不尊重家族中的长者。请陛下对他施以应有的惩罚!’
“于是,比丘们,阎魔王就第一个天的使者之事,质问、审察并对那人说:‘喂,善人,你难道从未见过第一个天的使者出现在人间吗?’
“他回答说:‘主公,我没有见过。’
“于是阎魔王对他说:‘但是,善人,你难道从未见过一个八十、九十或一百岁的男人或女人,身体衰弱,像屋梁一样弯曲,驼背,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疾病缠身,青春活力尽失,牙齿脱落,头发灰白稀疏或秃顶,满脸皱纹,四肢布满斑点吗?’
“那人回答说:‘是的,主公,我见过。’
“于是阎魔王对他说:‘善人,你作为一个有智慧的成年人,难道就没想过:“我也会衰老,无法逃避。我现在应当以身、语、意行持善业”吗?’
“‘主公,我没能做到。我放逸了。’
“于是阎魔王说:‘善人,因为放逸,你未能以身、语、意行持善业。好吧,你会因你的放逸而受到相应的处置。你所造的恶业,不是你的母亲或父亲、兄弟、姐妹、朋友或同伴所为,也不是亲戚、天人、沙门或婆罗门所为。而是你独自造了那恶业,你也必将承受其果报。’
“比丘们,当阎魔王就第一个天的使者之事,如此质问、审察并对他说完后,他又就第二个使者之事,质问、审察并对那人说:‘喂,善人,你难道从未见过第二个天的使者出现在人间吗?’
“‘主公,我没有见过。’
“‘但是,善人,你难道从未见过一个男人或女人,身患疾病,痛苦不堪,病重,躺在自己的污秽物中,需要别人扶起,需要别人安置上床吗?’
“‘是的,主公,我见过。’
“‘善人,你作为一个有智慧的成年人,难道就没想过:“我也会生病,无法逃避。我现在应当以身、语、意行持善业”吗?’
“‘主公,我没能做到。我放逸了。’
“‘善人,因为放逸,你未能以身、语、意行持善业。好吧,你会因你的放逸而受到相应的处置。你所造的恶业,不是你的母亲或父亲、兄弟、姐妹、朋友或同伴所为,也不是亲戚、天人、沙门或婆罗门所为。而是你独自造了那恶业,你也必将承受其果报。’
“比丘们,当阎魔王就第二个天的使者之事,如此质问、审察并对他说完后,他又就第三个使者之事,质问、审察并对那人说:‘喂,善人,你难道从未见过第三个天的使者出现在人间吗?’
“‘主公,我没有见过。’
“‘但是,善人,你难道从未见过一个死了一天、两天或三天的男人或女人的尸体,肿胀、变色、腐烂吗?’
“‘是的,主公,我见过。’
“‘那么,善人,你作为一个有智慧的成年人,难道就没想过:“我也会死亡,无法逃避。我现在应当以身、语、意行持善业”吗?’
“‘主公,我没能做到。我放逸了。’
“‘善人,因为放逸,你未能以身、语、意行持善业。好吧,你会因你的放逸而受到相应的处置。你所造的恶业,不是你的母亲或父亲、兄弟、姐妹、朋友或同伴所为,也不是亲戚、天人、沙门或婆罗门所为。而是你独自造了那恶业,你也必将承受其果报。’”
(出自 AN 3:35; I 138–40)
第二篇:无省思生活的苦恼
(1)苦受之箭
“比丘们,当未受教的凡夫经历苦受时,他会忧愁、悲伤、哀叹;他会捶胸顿足地哭泣,变得心烦意乱。他感受到两种受——一种是身体的,一种是心理的。譬如有人被一支箭射中,紧接着又被第二支箭射中,那人就会感受到由两支箭引起的感受。同样地,当未受教的凡夫经历苦受时,他感受到两种受——一种是身体的,一种是心理的。
“在经历那同样苦受的同时,他对它心怀厌恶。当他对苦受心怀厌恶时,对苦受的瞋恚随眠便潜伏于此。5在经历苦受时,他寻求欲乐之中的欢愉。是何原因?因为未受教的凡夫不知道除了欲乐之外,还有任何逃离苦受的方法。6当他寻求欲乐之中的欢愉时,对乐受的贪欲随眠便潜伏于此。他不能如实了知这些受的生起与息灭、味、患、离。7当他不了知这些事时,对不苦不乐受的无明随眠便潜伏于此。
“如果他感受到乐受,他是执着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到苦受,他是执着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到不苦不乐受,他是执着地感受它。比丘们,这被称为未受教的凡夫,他执着于生、老、死;执着于愁、悲、苦、忧、恼;我说,他执着于苦。
“比丘们,当已受教的圣弟子经历苦受时,他不会忧愁、悲伤、哀叹;他不会捶胸顿足地哭泣,也不会变得心烦意乱。8他只感受到一种受——一种身体的受,而非心理的受。譬如有人被一支箭射中,但紧接着没有被第二支箭射中,那人就只会感受到由一支箭引起的感受。同样地,当已受教的圣弟子经历苦受时,他只感受到一种受——一种身体的受,而非心理的受。
“在经历那同样苦受的同时,他对它不怀厌恶。由于他对苦受不怀厌恶,对苦受的瞋恚随眠便不会潜伏于此。在经历苦受时,他不会寻求欲乐之中的欢愉。是何原因?因为已受教的圣弟子知道除了欲乐之外,还有逃离苦受的方法。由于他不寻求欲乐之中的欢愉,对乐受的贪欲随眠便不会潜伏于此。他如实了知这些受的生起与息灭、味、患、离。由于他了知这些事,对不苦不乐受的无明随眠便不会潜伏于此。
“如果他感受到乐受,他是无执着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到苦受,他是无执着地感受它。如果他感受到不苦不乐受,他是无执着地感受它。比丘们,这被称为圣弟子,他已脱离生、老、死;脱离愁、悲、苦、忧、恼;我说,他已脱离苦。
“比丘们,这就是已受教的圣弟子与未受教的凡夫之间的区别、差异、不同之处。”
(SN 36:6; IV 207–10)
(2)世事变迁
“比丘们,这八种世间法让世界运转,世界也围绕这八种世间法运转。是哪八种?得与失,誉与毁,赞与讥,乐与苦。
“比丘们,未受教的凡夫会遇到这八种世间法,已受教的圣弟子也会遇到。那么,已受教的圣弟子与未受教的凡夫之间的区别、差异、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尊者,我们对这些事的了知根源于世尊;以世尊为引导和皈依处。尊者,若世尊能阐明此言的意义,那就太好了。比丘们听后会铭记于心。”
“那么,比丘们,谛听,仔细作意。我将要说。”
“是的,尊者。”比丘们回答道。世尊于是这样说:
“比丘们,当一个未受教的凡夫得到利得时,他不会这样思惟:‘我得到的这个利得是无常的,与苦相关,是会变异的。’他不能如实了知。当他遇到损失、声誉与毁誉、赞扬与指责时,他也不会这样思惟:‘所有这些都是无常的,与苦相关,是会变异的。’他不能如实了知它们。对于这样的人,得与失、誉与毁、赞与讥、乐与苦占据着他的心。得到时他兴高采烈,失去时他垂头丧气。得到声誉时他兴高采烈,遇到毁誉时他垂头丧气。得到赞扬时他兴高采烈,遇到指责时他垂头丧气。体验到快乐时他兴高采烈,体验到痛苦时他垂头丧气。如此纠缠于喜恶之中,他将无法从生、老、死,从愁、悲、苦、忧、恼中解脱;我说,他将无法从苦中解脱。
“但是,比丘们,当一个已受教的圣弟子得到利得时,他会这样思惟:‘我得到的这个利得是无常的,与苦相关,是会变异的。’当他遇到损失等情况时,他也会如此思惟。他如实了知所有这些事,它们不会占据他的心。因此,他不会因得而喜,因失而忧;因誉而喜,因毁而忧;因赞而喜,因讥而忧;因乐而喜,因苦而忧。如此舍弃了喜恶,他将从生、老、死,从愁、悲、苦、忧、恼中解脱;我说,他将从苦中解脱。
“比丘们,这就是已受教的圣弟子与未受教的凡夫之间的区别、差异、不同之处。”
(AN 8:6; IV 157–59)
(3)因变化而焦虑
“比丘们,我将教导你们因执取而激动,以及因不执取而不激动。9谛听并仔细作意。我将要说。”
“是的,尊者。”那些比丘回答道。世尊如此说道:
“比丘们,如何是因执取而激动?在此,比丘们,未受教的凡夫,他不见圣者,不善巧、不调伏于圣法;他不见善士,不善巧、不调伏于善士法,他视色为我,或我拥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10他的那个色变化、变异。随着色的变化和变异,他的识专注于色的变化。因专注于色的变化而产生的激动和一系列心所持续地困扰着他的心。因为他的心被困扰,他感到害怕、苦恼和焦虑,并通过执取而变得激动。
“他视受为我……想为我……行为我……识为我,或我拥有识,或识在我中,或我在识中。他的那个识变化、变异。随着识的变化和变异,他的识专注于识的变化。因专注于识的变化而产生的激动和一系列心所持续地困扰着他的心。因为他的心被困扰,他感到害怕、苦恼和焦虑,并通过执取而变得激动。
“比丘们,就是这样,因执取而有激动。
“比丘们,如何是因不执取而不激动?在此,比丘们,已受教的圣弟子,他见圣者,善巧、调伏于圣法;他见善士,善巧、调伏于善士法,他不视色为我,或我拥有色,或色在我中,或我在色中。11他的那个色变化、变异。尽管色有变化和变异,他的识并不会专注于色的变化。没有因专注于色的变化而产生的激动和一系列心所持续地困扰着他的心。因为他的心不被困扰,他不感到害怕、苦恼或焦虑,并通过不执取而不会变得激动。
“他不视受为我……想为我……行为我……识为我,或我拥有识,或识在我中,或我在识中。他的那个识变化、变异。尽管识有变化和变异,他的识并不会专注于识的变化。没有因专注于识的变化而产生的激动和一系列心所持续地困扰着他的心。因为他的心不被困扰,他不感到害怕、苦恼或焦虑,并通过不执取而不会变得激动。
“比丘们,就是这样,因不执取而无激动。”
(SN 22:7; III 15–18)
第三篇:动荡的世界
(1)冲突的根源
婆罗门阿拉玛丹达(Ārāmadaṇḍa)走近尊者摩诃迦旃延(Mahākaccāna),12与他互相友好问候后,问道:“迦旃延(Kaccāna)大师,为什么刹帝利与刹帝利争斗,婆罗门与婆罗门争斗,居士与居士争斗?”
“婆罗门,正是因为对欲乐的执着,对欲乐的依附,对欲乐的固执,对欲乐的沉溺,对欲乐的痴迷,对欲乐的坚守,所以刹帝利与刹帝利争斗,婆罗门与婆罗门争斗,居士与居士争斗。”
“迦旃延(Kaccāna)大师,为什么修行人与修行人争斗?”
“婆罗门,正是因为对见解的执着,对见解的依附,对见解的固执,对见解的沉溺,对见解的痴迷,对见解的坚守,所以修行人与修行人争斗。”
(AN 2: iv, 6, 节选; I 66)
(2)为何众生生活在仇恨中?
2.1. 天主释迦(Sakka),13问世尊:“众生希望无怨、无害、无敌、无仇地生活;他们希望和平地生活。然而他们却生活在仇恨中,互相伤害,彼此敌对,互为仇敌。尊者,他们是被什么束缚所缚,以致于如此生活?”
[世尊说:]“天主,是嫉妒和悭吝的束缚,束缚着众生,以致于他们虽然希望无怨、无敌、无仇地生活,希望和平地生活,却生活在仇恨中,互相伤害,彼此敌对,互为仇敌。”
这是世尊的回答,释迦(Sakka)欢喜地赞叹道:“正是如此,世尊!正是如此,善逝!通过世尊的回答,我已克服了我的疑惑,消除了我的不确定。”2.2. 然后,释迦(Sakka)在表示赞赏后,又问了另一个问题:“但是,尊者,是什么引起了嫉妒和悭吝,它们的根源是什么,它们是如何产生,如何生起的?当什么存在时它们会生起,当什么不存在时它们不会生起?”
“天主,嫉妒和悭吝源于喜与恶;这是它们的根源,这是它们产生、生起的方式。当这些存在时,它们就会生起,当这些不存在时,它们就不会生起。”
“但是,尊者,是什么引起了喜与恶……?”——“天主,它们源于欲望……”——“又是什么引起了欲望……?”——“天主,它源于思惟。当心思惟某事时,欲望就会生起;当心无所思惟时,欲望就不会生起。”
“但是,尊者,是什么引起了思惟……?”
“天主,思惟源于戏论想。14当戏论想存在时,思惟就会生起。当戏论想不存在时,思惟就不会生起。”
(出自 DN 21: Sakkapañha Sutta; II 276–77)
(3)黑暗的因果链
9.“阿难(Ānanda),因此,缘于受有爱;缘于爱有取;缘于取有得;缘于得有决策;缘于决策有欲与贪;缘于欲与贪有执着;缘于执着有占有;缘于占有有悭吝;缘于悭吝有守护;且因守护,各种邪恶不善法生起——拿起棍棒与武器、冲突、争吵与纠纷、侮辱、诽谤与谎言。”15
(出自 DN 15: Mahānidāna Sutta; II 58)
(4)暴力与压迫的根源
“各种贪、嗔、痴都是不善的。16一个贪婪、嗔恨、愚痴的人所积聚的任何行为——通过身、语、意——那也是不善的。这样一个被贪、嗔、痴所征服,思想被它们所控制的人,以虚假的借口对他人施加的任何痛苦——通过杀害、监禁、没收财产、诬告或驱逐——其动机是‘我有权力,我想要权力’的思想,所有这些也都是不善的。”
(出自 AN 3:69; I 201–2)
第四篇:无有可见的开端
(1)草与木棍
世尊说:“比丘们,这saṃsāra是无有可见的开端的。17被无明所障、被渴爱所缚的众生,其流转漂泊的最初一点是不可知的。比丘们,譬如有一个人,将这阎浮提(Jambudīpa)18中所有的草、木棍、树枝和树叶都砍下来,堆成一堆。做完之后,他每放下一根就说:‘这是我的母亲,这是我母亲的母亲。’那个人的母亲和祖母的序列将不会终结,而这阎浮提的草、木棍、树枝和树叶却会被用尽耗光。是何原因?因为,比丘们,这saṃsāra是无有可见的开端的。被无明所障、被渴爱所缚的众生,其流转漂泊的最初一点是不可知的。比丘们,如此长久以来,你们经历了苦、痛和灾难,填满了墓地。这足以让人对一切行法感到厌离,足以对它们离欲,足以从它们中解脱。”
(SN 15:1; II 178)
(2)泥球
“比丘们,这saṃsāra是无有可见的开端的。被无明所障、被渴爱所缚的众生,其流转漂泊的最初一点是不可知的。比丘们,譬如有一个人,将这片大地捏成枣核大小的泥球,每放下一个就说:‘这是我的父亲,这是我父亲的父亲。’那个人的父亲和祖父的序列将不会终结,而这片大地却会被用尽耗光。是何原因?因为,比丘们,这saṃsāra是无有可见的开端的。被无明所障、被渴爱所缚的众生,其流转漂泊的最初一点是不可知的。如此长久以来,你们经历了苦、痛和灾难,填满了墓地。这足以让人对一切行法感到厌离,足以对它们离欲,足以从它们中解脱。”
(SN 15:2; II 179)
(3)大山
某位比丘走近世尊,顶礼后,坐于一旁,对他说道:“尊者,一劫有多长?”19
“比丘,一劫很长。不容易计算它,说它有多少年,或多少百年,或多少千年,或多少十万年。”
“那么,尊者,能举个譬喻吗?”
“可以,比丘。”世尊说。“比丘,譬如有一座巨大的石山,长一由旬,宽一由旬,高一由旬,没有孔洞或裂缝,是整块的岩石。20每过一百年,就有人用一块细布擦它一次。通过这种努力,那座巨大的石山可能会被磨损殆尽,而一劫仍未结束。比丘,一劫就是这么长。而在如此长的劫中,我们已经流浪了许多劫,许多百劫,许多千劫,许多十万劫。是何原因?因为,比丘,这saṃsāra是无有可见的开端的……这足以从它们中解脱。”
(SN 15:5; II 181–82)
(4)恒河
在王舍城(Rājagaha)的竹林精舍,松鼠保护区,某位婆罗门走近世尊,与他互致问候。当他们结束问候和亲切交谈后,他坐于一旁,问他:“乔达摩(Gotama)大师,已经过去多少劫了?”
“婆罗门,已经过去很多劫了。不容易计算它们,说它们有多少劫,或多少百劫,或多少千劫,或多少十万劫。”
“但是,乔达摩(Gotama)大师,能举个譬喻吗?”
“婆罗门,这是可能的,”世尊说。“婆罗门,想象一下从恒河发源地到它汇入大海洋之间的沙粒:要数清它们并说出有多少沙粒、多少百粒、多少千粒、或多少百千粒,是不容易的。婆罗门,已经流逝过去的劫数比那还要多。要数清它们并说出有多少劫、多少百劫、多少千劫、或多少百千劫,是不容易的。是何原因?因为,婆罗门,这轮回无始……足以从中解脱。”
(SN 15:8; II 183–84)
(5)被拴住的狗
“比丘们,这轮回无始。众生被无明所障,被渴爱所缚,于其中流转轮回,其最初的起点是不可知的。
“比丘们,终有之时,大海洋会干涸、蒸发而不复存在,但我说,对于那些被无明所障、被渴爱所缚而流转轮回的众生,苦的终结仍然未到。
“比丘们,终有之时,须弥山王会燃烧、毁灭而不复存在,但我说,对于那些被无明所障、被渴爱所缚而流转轮回的众生,苦的终结仍然未到。
“比丘们,终有之时,大地会燃烧、毁灭而不复存在,但我说,对于那些被无明所障、被渴爱所缚而流转轮回的众生,苦的终结仍然未到。
“比丘们,譬如一只被绳索拴住的狗,被绑在一根坚固的柱子或桩子上:它只会绕着那同一根柱子或桩子不停地跑动和旋转。同样地,未受教导的凡夫视色为我……视受为我……视想为我……视行为我……视识为我……。他只是绕着色、受、想、行、识不停地跑动和旋转。当他不停地绕着它们跑动和旋转时,他便未从色解脱,未从受解脱,未从想解脱,未从行解脱,未从识解脱。他未从生、老、死解脱;未从愁、悲、苦、忧、恼解脱;我说,他未从苦中解脱。”
(SN 22:99; II 149–50)
注释
-
波斯匿王(King Pasenadi)是拘萨罗国(Kosala)的统治者,其首都是舍卫城(Sāvatthī)。祇陀林(Jetavana),即祇陀太子(Prince Jeta)的园林,也称为给孤独园(Anāthapindika’s Park),因为它是富有的慈善家给孤独长者(Anāthapindika)为佛陀购买的。《尼柯耶》将波斯匿王描绘为佛陀最虔诚的在家弟子之一,尽管书中从未显示他证得任何果位。《相应部》的整整一章——拘萨罗相应(第三章)——记录了他与佛陀的对话。 ↩
-
谈到阿罗汉时,佛陀并未将其命运描述为“老死”,而仅仅是身体的败坏和舍弃。这是因为阿罗汉已无任何“我”和“我的”观念,不认为身体的衰败和瓦解是某个“我”的老死。 ↩
-
Devadūta。根据传说,当菩萨还是一位生活在宫殿里的王子时,他遇到了一个老人、一个病人和一具尸体,这些是他以前从未见过的景象。这些遭遇打破了他对世俗的自满,并激励他去寻求一条从苦中解脱的道路。义注说,这三个人物是天人化身,被派来唤醒菩萨履行其使命。因此,老、病、死被称为“天使”。 ↩
-
阎摩(Yama)是传说中的地狱之神,他审判死者并决定他们未来的命运。根据一些说法,他只是在亡灵面前持一面镜子,镜子会映现出他们的善恶行为。 ↩
-
随眠(anusaya)是潜伏于心中、受激时才会活跃的烦恼倾向。某些经文,如本经,提到三种随眠:对乐受的贪爱随眠(rāgānusaya);对苦受的嗔恚随眠(paṭighānusaya);以及对不苦不乐受的无明随眠(avijjānusaya)。其他经文则提到七种随眠:欲贪、嗔恚、见、疑、慢、有贪及无明。 ↩
-
Spk:《相应部义注》:出离是指禅定、道与果。他不知道这些;他所知的唯一出离是感官之乐。 ↩
-
这五个术语构成了一个主要的禅修模式。“集与灭”(samudaya, atthaṅgama)指向无常的特性。关于味、患、离(assāda, ādīnava, nissaraṇa)三者,见第186–87页。 ↩
-
下文将清楚说明,这里所描述的“有闻圣弟子”是阿罗汉,唯有阿罗汉才能完全摆脱嗔恚、贪欲和无明的倾向。然而,虽然只有阿罗汉能够对身体的痛苦保持完美的舍,但普通修行者仍然可以效仿阿罗汉,在经历身体的苦受时,努力克服沮丧和绝望。每个有身体的人,包括佛陀在内,都会遭受身体的痛苦。能够忍受痛苦而不被其压倒,是修行成熟的标志。 ↩
-
名词 paritassanā 源自动词 paritassati,它对应梵语 paritṛṣyati,“渴求、渴望”;在词源上与渴爱(taṇhā)有关。然而,在巴利语中,该动词词干已与 tasati = 恐惧、颤抖相混淆,因此其名词派生词如 paritassanā 和 paritasita 也获得了源自 tasati 的含义。这种意义的融合在《尼柯耶》中已很明显,并在义注中被明确阐述。我尝试通过将动词 paritassati 译为“被搅动”和名词 paritassanā 译为“搅动”来捕捉这两种细微差别。尽管《相应部义注》在此处将 paritassanā 理解为渴爱,但经文似乎在强调 bhaya-paritassanā,“作为恐惧的搅动”。 ↩
-
无闻凡夫是指既缺乏对法的教理知识(由 akovida,“不通达”一词强调),也缺乏对法的实践训练(由 avinīta,“未调伏”一词强调)。凡夫不是“见圣者”,即不是佛陀和圣弟子的见证者,因为他缺乏洞察他们所见真理的智慧之眼。“圣者”(ariya)和“善人”(sappurisa)是同义词。本文在此列举了二十种身见(sakkāyadiṭṭhi),这是通过四种方式将自我与构成个人身份(sakkāya)的五蕴联系起来而产生的。身见是在入流(四种证悟阶段的第一阶段)时要断除的三个结之一。Spk:《相应部义注》:他视色为我(rūpaṃ attato samanupassati),即将色与我视为无差别,就像油灯的火焰与其颜色无差别一样。他视我为有色(rūpavantaṃ attānaṃ),当他将无色(即心或心所)视为拥有色的我,就像树拥有影子一样;色在我中(attani rūpaṃ),当他将无色(心)视为我,而色位于其中,就像花中有香气一样;我在色中(rūpasmiṃ attānaṃ),当他将无色(心)视为位于色中的我,就像珠宝在宝盒中一样。 ↩
-
这位圣弟子大概至少是入流者。 ↩
-
摩诃迦旃延(Mahākaccāna)是擅长详细分析佛陀简短开示的弟子。关于他的生平和教法,见向智长老与何克的《佛陀的大弟子》,第六章。 ↩
-
帝释(Sakka)是三十三天(Tāvatiṃsa)的统治者,他是佛陀的追随者。见SN第十一章。 ↩
-
Papañcasaññāsaṅkhā。这个晦涩复合词的含义在《尼柯耶》中没有阐明。该术语似乎指的是已被主观偏见“感染”,被渴爱、慢和扭曲的见解所“铺陈”的认知和观念。根据义注,渴爱、慢和见是导致概念铺陈(papañca)的三个因素。关于这个表达的详细研究见Ñāṇananda的《早期佛教思想中的概念与实相》(Concept and Reality in Early Buddhist Thought)。 ↩
-
Sv:《长部义注》:追寻(pariyesanā)是追寻可见色等境界,而获得(lābha)是获得这些境界。决断(vinicchaya)是决定自己保留多少、给予他人多少;使用多少、储存多少等等。 ↩
-
贪、嗔、痴(lobha, dosa, moha)是三种“不善根”——所有心所染污和不善行为的根本原因;见第146页。 ↩
-
Anamataggo ’yaṃ bhikkhave saṃsāro。anamatagga 的原始含义不确定。Spk:《相应部义注》将其解释为“具有不可寻的开端”,解释说:“即使以智慧追寻百千年,其开端亦不可寻,开端未知。不可能从这里或那里知道其开端;其意是说它没有限定的首尾点。轮回(Saṃsāra)是五蕴不间断相续的过程。” ↩
-
Jambudīpa。“阎浮提”,印度次大陆。 ↩
-
Kappa。这里指的似乎是一个 mahākappa,“大劫”,即一个世界系统从形成、发展到毁灭所需的时间。每个大劫由四个 asaṅkheyyakappa(无量劫)组成,即成、住、坏、空四个时期。关于早期佛教宇宙论的讨论,见盖辛(Gethin)的《佛教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Buddhism),第112–15页。 ↩
-
一由旬(yojana)约等于七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