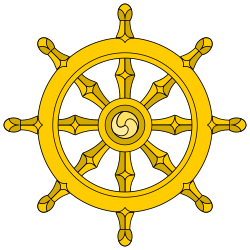Index
第八章:调伏自心

导言
在上一章对出世间道进行了广泛概述之后,在本章和下一章中,我打算更具体地关注《尼柯耶》中所描述的这条道路的两个方面:禅修和智慧。正如我们所见,次第训练分为戒、定、慧三个部分(见225-26页)。戒学始于遵守戒律,这将一个人的行为锚定在审慎行为和道德克制的原则上。受持戒律——对《尼柯耶》而言,特别是完整的僧伽戒律——被称为增上戒学(adhisīlasikkhā)。持续遵守的戒行,能以道德德行的净化力量注入内心,产生喜悦和对佛法更深的信心。
在戒行的基础上,弟子开始修习禅定,旨在稳定心,清除障碍智慧展现的因素。因为禅修将心提升至超越其常态的水平,这一修行阶段被称为增上心学(adhicittasikkhā)。因为它带来内心的宁静与寂静,也称为修习奢摩他(samathabh̄van̄)。成功的修习会带来深度的定或心一境性(samādhi),也称为内心奢摩他(ajjhattạ cetosamatha)。《尼柯耶》中认可的最卓越的定是四禅,它构成了八正道的正定(samm̄ sam̄dhi)。超越四禅的是四无色定(ar̄pasam̄patti),它将心一境性的过程带到更微细的层次。
修行的第三个阶段是增上慧学(adhipaññāsikkhā),旨在唤醒对佛陀教法所揭示的事物真实本质的直接洞见。这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下面第一篇选文,即第八章第一篇,是一些简短警句的杂集,强调了修心的必要性。这些语句成对出现。在每一对中,第一句指出了未修习之心的危险,第二句则赞颂了已修习之心的益处。未修习之心容易成为烦恼——贪、瞋、痴及其衍生物——的猎物。烦恼产生不善业,在今生和未来生中带来痛苦的结果。由于烦恼是我们痛苦和束缚的原因,解脱之道必然涉及一个细致的心灵训练过程,旨在制伏它们,并最终将它们从内心深处的巢穴中根除。由心的培育,产生快乐、自由与和平。
对于《尼柯耶》而言,培育心意味着培育奢摩他(samatha)和毗婆舍那(vipassanā)。第八章第二篇(1)说,当奢摩他得到培育时,它会导向定以及心从如贪欲和瞋恚等情感烦恼中解脱。当毗婆舍那得到培育时,它会导向洞察诸法真实本质的更高智慧,并永久地使心从无明中解脱。因此,掌控自心最需要的两件事是奢摩他和毗婆舍那。
由于定是智慧的基础,《尼柯耶》通常将培育奢摩他视为培育毗婆舍那的前导。然而,由于禅修者的根性不同,几部经文也允许了对这一顺序的替代方法。第八章第二篇(2)谈到了四种修心的方法:1. 第一种方法,也是经典的方法,是先培育奢摩他,后培育毗婆舍那。“奢摩他”意指四禅或(根据巴利义注)一种接近禅那的状态,称为“近行定”或“门槛定”(upacārasamādhi)。2. 第二种方法是先培育毗婆舍那,后培育奢摩他。由于没有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观智,这类禅修者——大概是智力敏锐的人——最初必须以定为基础,来获得对诸法真实特相的洞见。然而,这种定虽然足以产生观智,但似乎不足以突破至出世间道。因此,这些禅修者必须回到统一自心的任务上,然后才能继续观的工作。这种基于定的观智,最终将达到出世间道。3. 第三种方法是止观双运。采取这种方法的禅修者首先达到某个定的层次,如某个禅那或无色定,然后将其作为观的基础。在培育了观智之后,他们再回到定中,达到另一个禅那或无色定,并以此为观的基础。如此,他们不断前进,直到达到出世间道。4. 对第四种方法的描述有些模糊。经中说,“比丘的心被法义的掉举所攫住”,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获得定并达到出世间道。这种说法暗示了一个人最初被强烈的理解佛法的欲望所驱使,以至于他或她无法清晰地专注于任何禅修所缘。后来,在某些助缘的帮助下,这个人设法制伏了心,获得定,并达到出世间道。
第八章第二篇(3)再次确认了奢摩他和毗婆舍那都是必需的,并指出了各自修行所需的技巧。培育奢摩他需要稳定、平静、统一和专注内心的技巧。培育毗婆舍那需要观察、探究和辨别有为法(被称为“行” saṅkhārā)的技巧。与前文一致,这部经确认了一些禅修者从培育内心奢摩他开始,另一些人从培育洞察诸法的更高智慧开始,还有一些人则两者双运。但是,虽然禅修者的起点可能不同,最终他们都必须在奢摩他和毗婆舍那之间取得健康的平衡。两者之间确切的平衡点因人而异,但当禅修者达到适当的平衡时,奢摩他和毗婆舍那会合力产生对四圣谛的知见。这种知见——出世间的智慧——以四个不同的“阶段”发生,这四个证悟阶段,依次永久地摧毁无明以及相关的烦恼。1 第八章第二篇(2)将这些烦恼归纳在“结与随眠”这一表述之下。
培育奢摩他和毗婆舍那的主要障碍被统称为“五盖”,我们已经在次第训练的详细描述中遇到过(见第七章第四篇 §18)。第八章第三篇指出,就像水中不同的杂质使我们无法清晰地看到脸在水盆中的倒影一样,五盖也使我们无法正确地理解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因此,禅修者最初的努力必须致力于克服五盖的任务。一旦这些被克服,奢摩他和毗婆舍那的修行就必将成功。
第八章第四篇将心的相继净化过程比作黄金的提炼。禅修的比丘开始时,要去除身、语、意行为的粗重杂染;这是通过戒行和警觉的内省来实现的。然后,他消除中等层次的杂染,即不善的思惟:欲思惟、瞋思惟和害思惟。接下来是微细的杂染,即散漫的思惟。最后,他必须消除关于佛法的思惟,这是最微细的障碍。当所有这些分心的思惟都被去除后,比丘达到“心一境性”(ekodibhāva),这是六神通(abhiññā)的基础,最终导向阿罗汉果位,即漏尽智。
尼柯耶有时将训练心的过程比作驯服野生动物。就像驯兽师必须使用各种技巧来控制动物一样,禅修者也必须借助各种方法来调伏自心。仅仅熟悉一种禅修技巧是不够的;一个人必须熟练掌握多种方法,以作为对治特定心理障碍的良方。在第八章第五篇的经文中,佛陀解释了五种辅助技巧——这里称为“相”(nimitta)——比丘可以用来消除与贪、嗔、痴相关的不善念。通过使用这些技巧成功克服散乱念头的人,被称为“思惟过程的主宰者”。
经中教导了各种旨在引发禅定的禅修技巧。一个普遍的法门是将特定的禅修所缘与它们旨在纠正的不善心所状态相对治。因此,对身体不净性质的禅修(见第八章第八篇第10节)是对治贪欲的良方;慈心是对治嗔恚的良方;安那般那念是对治掉举的良方;而无常想则是对治“我是”我慢的良方。2 无常想是观禅的所缘,其他三种则是止禅的所缘。慈心是第五章简要讨论过的四梵住(brahmavihāra)或四无量心(appamaññā)中的第一个:无量的慈、悲、喜、舍。它们分别是对治嗔恚、伤害、不满和偏袒的良药。由于我们已经在讨论作为功德基础的禅修时,介绍了关于四梵住的标准经文——见第五章第五篇第2节——为了从不同角度阐明这一修行,我在此收录了著名的《锯喻经》,作为第八章第六篇的经文,这段经文展示了慈心在行动中的体现。
几个世纪以来,在居士中最受欢迎的禅修所缘可能是六随念(anussati):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第八章第七篇的经文是关于这些禅修的重要经典来源。它们的主题尤其贴近在充满佛教价值观的文化中过着家庭生活的人们的心灵和日常经验。这些禅修实践反过来又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生活,使他们与宗教信仰的理想在修行上有了更紧密的联系。前三者主要是基于对三宝信心的虔诚随念;但它们虽始于信,却能暂时净化心的烦恼,并有助于持续的专注。对戒德的禅修是从个人持守戒律发展而来的,这是一种自利的修行;对布施的随念建立在个人行施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利他的修行;对天人的随念是对个人信、戒、施、慧的果报在未来生命中成熟的思惟。
通常被认为提供了最全面禅修指导的经是《念住经》。3 这部经有两个版本,一个较长的版本在《长部》,一个中等长度的版本在《中部》。前者与后者的区别仅在于其对四圣谛的扩展分析,这可能最初是一篇早期的义注被并入了经文中。此处收录的是中等长度的版本,即第八章第八篇的经文。《相应部》中有一整品,即《念住相应》,也专门论述了这一禅修体系。
《念住经》并未推荐单一的禅修所缘,甚至没有推荐单一的禅修方法。其目的,毋宁说是为了解释如何建立证悟涅槃所需的观照模式。如经题所示,需要建立的恰当心境被称为“念住”。satipaṭṭhāna 这个词或许应被理解为 sati(念)和 upaṭṭhāna(住立)的复合词;因此,“念住”可能是最能捕捉其原意的翻译。根据伴随每个练习的标准模式,念住是一种安住(viharati)的模式。这种安住模式涉及以恰当的心境观察所缘。这种心境由三种积极的品质构成:精勤(ātāpa,“热忱”)、念(sati)和明晰知见(sampajañña)。sati 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记忆,但在当前语境中,它表示对当下的忆念,一种对我们在每个经验时刻,发生在我们身上和内在的事物的持续觉知。念,在其初始阶段,关注于使观照的心持续地专注于其所缘,这意味着使所缘持续地呈现于心。念防止心溜走,防止在散乱念头的影响下漂移到心理增殖和遗忘中。念通常被认为与“明晰知见”紧密结合发生,这是一种对自己正在经历的事情的清晰了知和理解。
经的开篇模式说,一个人在“已于世间调伏贪忧”(vineyya loke abhijjhā-domanassaṃ)之后,才从事这项修行。短语“已调伏”不必被理解为一个人必须首先克服贪与忧——根据义注,这表示贪婪与厌恶,因此代表五盖——然后才能开始修习念住。这个短语可以理解为,修行本身就是克服贪与忧的方法。因此,在调伏贪与嗔的障碍性影响的同时,禅修者激发起精勤、念和明晰知见的积极品质,并观照四个所缘范围:身、受、心、法。正是这四个所缘范围将念住的观察区分为四念住。
四个所缘范围将《念住经》的阐述部分分为四个主要章节。其中两个章节,即第一和第四章,有几个小节。当这些部分加在一起时,我们总共得到二十一个禅修所缘。其中一些可以作为培育止(samatha)的方法,但整个念住体系似乎特别为培育观而设计。主要章节及其划分如下:1. 身随观念(kāyānupassanā)。这包括十四个禅修所缘:安那般那念;四威仪的观照;对活动的明晰知见;对身体不净性质的作意(通过其器官和组织来观察);对界的作意;以及九种冢间观,即基于不同腐烂阶段尸体的观照。2. 受随观念(vedanānupassanā)。受被区分为三种主要类型——乐、苦和不苦不乐——每一种又进一步区分为肉体的受和精神的受。然而,因为这些都只是不同类型的受,所以受随观被认为是一个所缘。3. 心随观念(cittānupassanā)。这是一个观照的所缘——心——被区分为八对相反的心所状态。4. 法随观念(dhammānupassanā)。这里的 dhammā 一词可能指诸法,这些法被归入由佛陀的教法(Dhamma)所统摄的五个类别。因此,dhammānupassanā 有双重含义,“以法(教法)来观照诸法(现象)”。这五个类别是:五盖、五蕴、六内外处、七觉支和四圣谛。
尽管经中没有明确说明,但描述每一种观照的术语似乎暗示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序列。在安那般那念中,一个人进入更微细的寂静层次;在受随观中,一个人趋向于非肉体的、既非苦亦非乐的受;在心随观中,一个人趋向于专注和解脱的心所状态。这些都表明,渐进的观照会带来增强的定力。在法随观中,重点转向了观。一个人从观察和克服五盖开始。克服五盖标志着在定力上的成功。以专注之心,一个人观照五蕴和六处。随着观照势头的增强,七觉支显现出来,而七觉支的培育最终导向对四圣谛的了知。对四圣谛的了知使心从烦恼中解脱出来,从而导向涅槃的证得。因此,这一禅修体系实现了佛陀所说的它能直接导向涅槃实证的潜力。
每个主要的观照练习都辅以一个辅助部分,一个有四个小节的“副歌”。第一部分指出,禅修者于内观照所缘(在自己的经验中),于外观照(反思性地思考它发生在他人经验中),以及内外皆观;这确保了人对所缘获得全面而均衡的看法。第二部分指出,禅修者观照所缘为缘起之法,为坏灭之法,以及既缘起又坏灭之法;这揭示了无常的特相,从而导向对三法印的洞见:无常、苦、无我(anicca, dukkha, anattā)。第三部分指出,禅修者只是单纯地觉知赤裸的所缘,达到持续的念与知所必需的程度。第四部分描述禅修者安住于一种完全无著的状态,不执取世间的任何事物。
在《念住经》中,安那般那念(ānāpānasati)仅作为众多禅修所缘之一被收录,但尼柯耶赋予它根本的重要性。佛陀说他曾用安那般那念作为他证悟的主要禅修所缘(见SN 54:8; V 317)。在他教导生涯中,他偶尔会独处,致力于“通过安那般那念获得的定”,并通过称之为“如来住”而赋予其独特的尊荣(SN 54:11; V 326)。
安那般那念是《相应部》中一整品(SN 54, Ānāpānasaṃyutta)的主题。鉴于《念住经》用一个四步法来解释安那般那念,而该相应部中的诸经则将其修行扩展至十六个步骤。第八章第九篇的经文,来自《安那般那相应》,描述了这十六个步骤。由于这些步骤不一定是顺序的,而是部分重叠,它们可以被看作是面向而不是实际的步骤。这十六个面向被分为四个四法组,每个四法组对应四念住之一。第一个四法组包含了《念住经》在其身随观部分提到的四个面向,但其他四法组将修行扩展到对受、心、法的观照。因此,安那般那念的培育不仅可以圆满一个,而是可以圆满所有四个念住。基于安那般那念的四念住,又依次圆满七觉支;而这些又依次圆满明与解脱。这一阐述因此显示,安那般那念是一个完整的禅修所缘,它始于对呼吸的简单专注,并最终导向心的永久解脱。
最后,在第八章第十篇的经文中,佛陀的上首弟子舍利弗(Sāriputta)尊者,为自己掌控自心的成就作证。在回答阿难(Ānanda)尊者的问题时,他解释了自己如何能够在每个禅那和无色定中安住一整天,以及在名为想受灭尽定(saññāvedayitanirodha)的特殊定中安住。在每种情况下,因为他是一位阿罗汉,他都能做到这一点而不用“我”和“我的”念头去执取这些定境。
第一篇:心是关键
1. “诸比丘,我未见有任何一法,像未培育的心那样难调伏。未培育的心确实是难调伏的。
2. “诸比丘,我未见有任何一法,像已培育的心那样易调伏。已培育的心确实是易调伏的。
3. “诸比丘,我未见有任何一法,像未培育的心那样导致巨大的伤害。未培育的心会导致巨大的伤害。
4. “诸比丘,我未见有任何一法,像已培育的心那样导致巨大的助益。已培育的心会导致巨大的助益。
9. “诸比丘,我未见有任何一法,当未培育和未修习时,会像心那样带来巨大的痛苦。当未培育和未修习时,心会带来巨大的痛苦。
10. “诸比丘,我未见有任何一法,当已培育和已修习时,会像心那样带来巨大的安乐。当已培育和已修习时,心会带来巨大的安乐。”
(增支部 AN 1: iii, 1, 2, 3, 4, 9, 10; I5–6)
第二篇:培育一对技能
(1)止与观
“诸比丘,有二法与明有关。是哪二法?止与观。
“当止被培育时,人会体验到什么助益?心被培育。当心被培育时,人会体验到什么助益?一切贪欲被断除。4
“当观被培育时,人会体验到什么助益?智慧被培育。当智慧被培育时,人会体验到什么助益?一切无明被断除。5
“被贪欲染污的心不得解脱;被无明染污的智慧不得培育。因此,诸比丘,通过贪欲的消退而有心解脱;通过无明的消退而有慧解脱。”6
(增支部 AN 2: iii, 10; I 61)
(2)证得阿罗汉的四种方式
如是我闻。一时,阿难(Ānanda)尊者住在憍赏弥(Kosambī)的瞿师罗园(Ghosita’s monastery)。在那里,阿难尊者对诸比丘说:
“朋友们!”
“是的,朋友。”诸比丘回答道。于是阿难尊者说:
“朋友们,任何在我面前宣称已证得阿罗汉最终智的比丘或比丘尼,都是通过四种方式之一做到的。是哪四种?
“于此,朋友们,有比丘修习观先行于止。7 当他这样修习观先行于止时,道在他心中生起。他接着追随、培育并修习那道,当他这样做时,诸结被断除,随眠被根除。8
“再者,朋友们,有比丘修习止先行于观。9 当他这样修习止先行于观时,道在他心中生起。他接着追随、培育并修习那道,当他这样做时,诸结被断除,随眠被根除。
“再者,朋友们,有比丘止观双运修习。10 当他这样止观双运修习时,道在他心中生起。他接着追随、培育并修习那道,当他这样做时,诸结被断除,随眠被根除。
“再者,朋友们,有比丘的心为法所激动。11 但到某个时候,他的内心得以安定、沉静、合一与专注;那时道在他心中生起。他接着追随、培育并修习那道,当他这样做时,诸结被断除,随眠被根除。
“朋友们,任何在我面前宣称已证得阿罗汉最终智的比丘或比丘尼,都是通过这四种方式之一做到的。”
(增支部 AN 4:170; II 156–57)
(3)四种人
“诸比丘,世间存在这四种人。是哪四种?
“于此,诸比丘,某人获得了内心的止,但未获得对诸法的上等观慧。12 另一人获得了对诸法的上等观慧,但未获得内心的止。另一人既未获得内心的止,也未获得对诸法的上等观慧。还有另一人既获得了内心的止,也获得了对诸法的上等观慧。
“其中,诸比丘,那获得内心的止但未获得对诸法的上等观慧之人,应去亲近那获得上等观慧之人,并询问他:‘朋友,应如何看待诸行?应如何审察诸行?应如何以观慧辨识诸行?’13 另一人便如他所见所解那样回答他:‘诸行应如此看待;应如此审察;应如此以观慧辨识。’之后某个时候,此人便既获得了内心的止,也获得了对诸法的上等观慧。
“其中,诸比丘,那获得对诸法的上等观慧但未获得内心的止之人,应去亲近那获得内心的止之人,并询问他:‘朋友,应如何使心安定?应如何使心沉静?应如何使心合一?应如何使心专注?’另一人便如他所见所解那样回答他:‘心应如此安定,如此沉静,如此合一,如此专注。’之后某个时候,此人便既获得了内心的止,也获得了对诸法的上等观慧。
“其中,诸比丘,那既未获得内心的止也未获得对诸法的上等观慧之人,应去亲近那两者兼得之人,并询问他:‘朋友,应如何使心安定?……朋友,应如何看待诸行?……’另一人便如他所见所解那样回答他:‘心应如此安定……诸行应如此看待……’之后某个时候,此人便既获得了内心的止,也获得了对诸法的上等观慧。
“其中,诸比丘,那既获得了内心的止又获得了对诸法的上等观慧之人,应安住于这些善法中,并为断除诸漏作进一步的努力。”
(增支部 AN 4:94; II 93–95)
第三篇:修行的障碍
那时,婆罗门商伽罗婆(Saṅgārava)走近世尊,与他互相问候后,坐在一旁说:
“乔达摩(Gotama)大师,为什么有时候,即使是长久诵习过的经文也无法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未曾诵习过的?又为什么有时候,即使是长久未曾诵习过的经文也能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已经诵习过的?”
“婆罗门,当一个人住于心被欲欲所占据、被欲欲所压倒,且不能如实了知对已生起的欲欲之出离时,14 在那种情况下,他既不如实知见自己的利益,也不如实知见他人的利益,或两者的利益。那时,即使是长久诵习过的经文也无法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未曾诵习过的。
“譬如,婆罗门,有一碗水,混有红色、黄色、蓝色或深红色的染料。如果一个视力好的人想在其中察看自己的面容影像,他将无法如实地知见它。同样地,婆罗门,当一个人住于心被欲欲所占据时……即使是长久诵习过的经文也无法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未曾诵习过的。
“再者,婆罗门,当一个人住于心被嗔恚所占据、被嗔恚所压倒,且不能如实了知对已生起的嗔恚之出离时,在那时,他既不如实知见自己的利益,也不如实知见他人的利益,或两者的利益。那时,即使是长久诵习过的经文也无法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未曾诵习过的。
“譬如,婆罗门,有一碗水在火上加热,沸腾翻滚。如果一个视力好的人想在其中察看自己的面容影像,他将无法如实地知见它。同样地,婆罗门,当一个人住于心被嗔恚所占据时……即使是长久诵习过的经文也无法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未曾诵习过的。
“再者,婆罗门,当一个人住于心被昏沉睡眠所占据、被昏沉睡眠所压倒,且不能如实了知对已生起的昏沉睡眠之出离时,在那时,他既不如实知见自己的利益,也不如实知见他人的利益,或两者的利益。那时,即使是长久诵习过的经文也无法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未曾诵习过的。
“譬如,婆罗门,有一碗水被水生植物和藻类覆盖。如果一个视力好的人想在其中察看自己的面容影像,他将无法如实地知见它。同样地,婆罗门,当一个人住于心被昏沉睡眠所占据时……即使是长久诵习过的经文也无法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未曾诵习过的。
“再者,婆罗门,当一个人住于心被掉举恶作所占据、被掉举恶作所压倒,且不能如实了知对已生起的掉举恶作之出离时,在那时,他既不如实知见自己的利益,也不如实知见他人的利益,或两者的利益。那时,即使是长久诵习过的经文也无法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未曾诵习过的。
“譬如,婆罗门,有一碗水被风吹动,泛起涟漪,旋转,搅成微波。如果一个视力好的人想在其中察看自己的面容影像,他将无法如实地知见它。同样地,婆罗门,当一个人住于心被掉举恶作所占据时……即使是长久诵习过的经文也无法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未曾诵习过的。
“再者,婆罗门,当一个人住于心被疑所占据、被疑所压倒,且不能如实了知对已生起的疑之出离时,在那时,他既不如实知见自己的利益,也不如实知见他人的利益,或两者的利益。那时,即使是长久诵习过的经文也无法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未曾诵习过的。
“譬如,婆罗门,有一碗水,浑浊、未静、泥泞,放置在黑暗中。如果一个视力好的人想在其中察看自己的面容影像,他将无法如实地知见它。同样地,婆罗门,当一个人住于心被疑所占据时……即使是长久诵习过的经文也无法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未曾诵习过的。
“婆罗门,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长久诵习过的经文也无法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未曾诵习过的原因。
“婆罗门,当一个人住于心不被欲欲、嗔恚、昏沉睡眠、掉举恶作和疑所占据时,在那时,即使是长久未曾诵习过的经文也能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已经诵习过的。
“譬如,婆罗门,有一碗水,没有混入染料;没有沸腾翻滚;没有被水生植物和藻类覆盖;没有被风吹动和搅成微波;清澈、宁静、澄明,放置在光亮处。如果一个视力好的人想在其中察看自己的面容影像,他将会如实地知见它。同样地,婆罗门,当一个人住于心不被欲欲、嗔恚、昏沉睡眠、掉举恶作和疑所占据时,在那时,即使是长久未曾诵习过的经文也能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已经诵习过的。
“婆罗门,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长久未曾诵习过的经文也能浮现于心,更不用说那些已经诵习过的原因。”……
此番话后,婆罗门商伽罗婆对世尊说:“太殊胜了,乔达摩大师!……请乔达摩大师接受我为一名居士,从今日起直至生命终结,皆皈依三宝。”
(相应部 SN 46:55, 节选; V 121–26)
第四篇:心的净化
“诸比丘,黄金中有粗大的杂质,如土和沙、砾石和砂砾。现在,金匠或他的学徒首先将金倒入槽中,彻底地洗涤、漂洗和清洁它。当他做完这些后,黄金中仍有中等的杂质,如细砂砾和粗沙。然后金匠或他的学徒再次洗涤、漂洗和清洁它。当他做完这些后,黄金中仍有微细的杂质,如细沙和黑尘。现在金匠或他的学徒重复洗涤,此后只剩下金粉。
“他现在将黄金倒入熔锅中,冶炼并熔化它。但他还未将它从容器中取出,因为浮渣尚未完全去除,黄金也还不够柔软、堪用和明亮;它仍然易碎,不易于塑形。但到某个时候,金匠或他的学徒会彻底重复熔炼,以便瑕疵完全去除。现在的黄金非常柔软、堪用和明亮,并且易于塑形。无论金匠现在希望用它制作何种饰品,无论是头冠、耳环、项链或金链,现在的黄金都可用于该目的。
“诸比丘,这与致力于修习增上心的比丘相似:他有粗大的杂质,即身、语、意的不善行。这样的行为,一位认真、有能力的比丘会舍弃、驱散、消除和废除。
“当他舍弃了这些之后,仍有中等程度的杂质依附于他,即欲思惟、嗔思惟和害思惟。15 这样的思惟,一位认真、有能力的比丘会舍弃、驱散、消除和废除。
“当他舍弃了这些之后,仍有一些微细的杂质依附于他,即关于他的亲属、他的国家和他的名声的思惟。这样的思惟,一位认真、有能力的比丘会舍弃、驱散、消除和废除。
“当他舍弃了这些之后,仍然有关于法的思惟。16 这样的定还不是平和与殊胜的;它尚未达到完全的寂静,也未实现心的合一;它是由对烦恼的费力压制来维持的。
“但到某个时候,他的内心得以安定、沉静、合一与专注。那时的定是平静与精炼的;它已达到完全的寂静并实现了心的合一;它不是由对烦恼的费力压制来维持的。
“然后,无论他将心导向何种可通过证智实现的心理状态,只要必要条件具备,他便能获得通过证智实现该状态的能力。17
“如果他希望:‘愿我能运用各种神通力:由一变多,由多变一;显现与消失;穿墙、穿壁、穿山无碍,如行于空中;出入大地如在水中;履水不沉如行于地;跏趺坐于空中飞行如鸟;以手触摸日月,如此强大有力;以身行使威力远至梵天界’——只要必要条件具备,他便能获得通过证智实现该状态的能力。
“如果他希望:‘以清净超人的天耳界,愿我能听到两种声音,天界的和人间的,远的和近的’——只要必要条件具备,他便能获得通过证智实现该状态的能力。
“如果他希望:‘愿我能以自己的心,了知其他众生、他人的心。愿我能了知有贪的心为有贪的心;无贪的心为无贪的心;有瞋的心为有瞋的心;无瞋的心为无瞋的心;有痴的心为有痴的心;无痴的心为无痴的心;收缩的心为收缩的心,散乱的心为散乱的心;广大的心为广大的心,不广大的心为不广大的心;有上的心为有上的心,无上的心为无上的心;得定的心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为未得定的心;解脱的心为解脱的心,未解脱的心为未解脱的心’——只要因缘具足,他便能以亲证实现那种境界。
“如果他希望:‘愿我能忆起种种过去生……[见第二章第三篇(2)§38]……其情状与细节’——只要因缘具足,他便能以亲证实现那种境界。
“如果他希望:‘愿我以清净、超越人眼的天眼,看见众生死时生时,低劣与高尚、美丽与丑陋、幸运与不幸……[见第二章第三篇(2)§40]……并了知众生如何随其业而轮转’——只要因缘具足,他便能以亲证实现那种境界。
“如果他希望:‘愿我以诸漏的灭尽,就在此生中,亲证、进入和安住于无漏的心解脱、慧解脱’——只要因缘具足,他便能以亲证实现那种境界。”
(AN 3:100 §§1–10; I 253–56)
第五篇:平息散乱的念头
1.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舍卫城(Sāvatthī)祇陀林(Jeta’s Grove)给孤独园(Anāthapiṇḍika’s Park)。在那里,他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尊者。”他们回答道。世尊如此说道:
2. “诸比丘,当一位比丘在修习增上心时,应时时作意五种相。18是哪五种?
3. (一) “于此,诸比丘,当一位比丘作意某种相,而由于那种相,他心中生起了与贪、瞋、痴相应的邪恶不善念头,那么他应当作意另一种与善相应的相。19当他作意另一种与善相应的相时,那么任何与贪、瞋、痴相应的邪恶不善念头都会在他心中被舍断并平息。随着它们的舍断,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就像一位熟练的木匠或他的学徒,用一根细木钉敲出、移除并拔掉一根粗木钉一样,同样地……当一位比丘作意另一种与善相应的相时……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
4. (二) “如果当他作意另一种与善相应的相时,心中仍然生起与贪、瞋、痴相应的邪恶不善念头,那么他应当审察那些念头的过患:‘这些念头是不善的、应受谴责的、会导致苦的。’当他审察那些念头的过患时,那么任何与贪、瞋、痴相应的邪恶不善念头都会在他心中被舍断并平息。随着它们的舍断,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就像一个年轻、青春、喜爱装饰的男人或女人,如果脖子上被挂上蛇、狗或人的尸体,他或她会感到惊恐、羞辱和厌恶一样,同样地……当一位比丘审察那些念头的过患时……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
5. (三) “如果当他审察那些念头的过患时,心中仍然生起与贪、瞋、痴相应的邪恶不善念头,那么他应当尝试忘掉那些念头,不应作意它们。当他尝试忘掉那些念头而不作意它们时,那么任何与贪、瞋、痴相应的邪恶不善念头都会在他心中被舍断并平息。随着它们的舍断,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就像一个视力良好的人,不想看见进入视野的色法时,他会闭上眼睛或移开视线一样,同样地……当一位比丘尝试忘掉那些念头而不作意它们时……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
6. (四) “如果当他尝试忘掉那些念头而不作意它们时,心中仍然生起与贪、瞋、痴相应的邪恶不善念头,那么他应当作意止息那些念头的行。20当他作意止息那些念头的行时,那么任何与贪、瞋、痴相应的邪恶不善念头都会在他心中被舍断并平息。随着它们的舍断,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就像一个走得快的人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走这么快?如果我慢走呢?’然后他就会慢走;然后他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慢走?如果我站着呢?’然后他就会站着;然后他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站着?如果我坐下呢?’然后他就会坐下;然后他可能会想:
‘我为什么要坐着?如果我躺下呢?’然后他就会躺下。通过这样做,他用一种更细微的威仪取代了每一种更粗重的威仪。同样地……当一位比丘作意止息那些念头的行时……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
7. (五) “如果当他作意止息那些念头的行时,心中仍然生起与贪、瞋、痴相应的邪恶不善念头,那么,他应当咬紧牙关,舌抵上颚,以心制心、约束心、粉碎心。当他咬紧牙关,舌抵上颚,以心制心、约束心、粉碎心时,那么任何与贪、瞋、痴相应的邪恶不善念头都会在他心中被舍断并平息。随着它们的舍断,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就像一个强壮的人抓住一个较弱的人的头或肩膀,将他击倒、制伏、压碎一样,同样地……当一位比丘咬紧牙关,舌抵上颚,以心制心、约束心、粉碎心时……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
8. “诸比丘,当一位比丘作意某种相,而由于那种相,他心中生起了与贪、瞋、痴相应的邪恶不善念头时,那么当他作意另一种与善相应的相时,任何这类邪恶不善念头都会在他心中被舍断并平息,随着它们的舍断,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当他审察那些念头的过患时……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当他尝试忘掉那些念头而不作意它们时……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当他作意止息那些念头的行时……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当他咬紧牙关,舌抵上颚,以心制心、约束心、粉碎心时,任何这类邪恶不善念头都会在他心中被舍断并平息,随着它们的舍断,他的心便在内安住、平息、专一、得定。这位比丘于是被称为掌控各种念头行的大师。他想思考什么念头就能思考什么,不想思考的任何念头便不会思考。他已斩断渴爱,抛开诸结,并以完全彻见我慢而灭尽了苦。”
此为世尊所说。诸比丘心满意足,欢喜世尊所说。
(MN 20: Vitakkasaṇṭhāna Sutta; I 118–22)
第六篇:慈心
11. “诸比丘,当他人对你们说话时,可能会使用五种言语方式:他们的话语可能适时或不适时,真实或不真实,温和或粗暴,与善相应或与恶相应,以慈心说或以瞋恨心说。当他人对你们说话时,他们的话语可能适时或不适时;当他人对你们说话时,他们的话语可能真实或不真实;当他人对你们说话时,他们的话语可能温和或粗暴;当他人对你们说话时,他们的话语可能与善相应或与恶相应;当他人对你们说话时,他们的话语可能以慈心说或以瞋恨心说。于此,诸比丘,你们应当如此训练:‘我们的心将保持不受影响,我们绝不出恶言;我们将为了他们的福祉而安住于慈悲,怀着慈心,绝不怀有瞋恨。我们将以充满慈爱的心遍满那个人而安住,并从那个人开始,21我们将以充满慈爱的心,丰盛、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地遍满一切世界而安住。’诸比丘,你们应当如此训练……。
20. “诸比丘,即使盗贼用双柄锯残忍地将你们的肢体逐一锯断,那对他们生起瞋恨心的人,也不是在奉行我的教法。于此,诸比丘,你们应当如此训练:‘我们的心将保持不受影响,我们绝不出恶言;我们将为了他们的福祉而安住于慈悲,怀着慈心,绝不怀有瞋恨。我们将以充满慈爱的心遍满他们而安住;并从他们开始,我们将以充满慈爱的心,丰盛、广大、无量、无敌意、无恶意地遍满一切世界而安住。’诸比丘,你们应当如此训练。
21. “诸比丘,如果你们将这关于锯子譬喻的忠告时时谨记在心,你们可见有任何言语,无论微小或粗重,是你们所不能忍受的吗?”——“没有,尊者。”——“因此,诸比丘,你们应当将这关于锯子譬喻的忠告时时谨记在心。这将为你们带来长久的福祉与快乐。”
(from MN 21: Kakacūpama Sutta; I 126–27, 129)
第七篇:六随念
一时,世尊住在迦毗罗卫城(Kapilavatthu)的榕树园(Banyan-tree Monastery)。那时,释迦族人摩诃男(Mahānāma)前来拜见世尊,向他行礼后,坐在一旁说:22
“尊者,当一位圣弟子证得圣果、了悟教法时,他以何种方式常安住呢?”23
“摩诃男,当一位圣弟子证得圣果、了悟教法时,他常如此安住。于此,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如来:‘世尊是阿罗汉、正自觉者、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当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如来时,在那一刻,他的心不被贪、瞋、痴所困扰;他的心是正直的,以如来为所缘。心正直的圣弟子获得义的启发、法的启发,获得与法相连的喜悦。当他喜悦时,喜(pīti)便生起;对于为喜所振奋的人,身体变得轻安;身体轻安的人感到乐;快乐的人,心便得定。这被称为一位在不平等的众生中平等安住,在有苦恼的众生中无苦恼安住的圣弟子,他已入于法流并培育佛随念。
“再者,摩诃男,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法:‘法由世尊善说,是自见的、无时节的、来见的、引导的、智者可亲身体证的。’当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法时,在那一刻,他的心不被贪、瞋、痴所困扰;他的心是正直的,以法为所缘……。这被称为一位在不平等的众生中平等安住,在有苦恼的众生中无苦恼安住的圣弟子,他已入于法流并培育法随念。
“再者,摩诃男,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僧伽:‘世尊的弟子僧团是行善道者,行直道者,行真道者,行正道者;即四双八辈——这世尊的弟子僧团是值得供养者,值得款待者,值得布施者,值得合十敬礼者,是世间的无上福田。’当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僧伽时,在那一刻,他的心不被贪、瞋、痴所困扰;他的心是正直的,以僧伽为所缘……。这被称为一位在不平等的众生中平等安住,在有苦恼的众生中无苦恼安住的圣弟子,他已入于法流并培育僧随念。
“再者,摩诃男,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他自己的戒行:‘我拥有圣者所喜爱的戒德,不破、不穿、无瑕、无疵、能解脱、为智者所赞叹、不为执取、能导向定。’当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他自己的戒行时,在那一刻,他的心不被贪、瞋、痴所困扰;他的心是正直的,以戒为所缘……。这被称为一位在不平等的众生中平等安住,在有苦恼的众生中无苦恼安住的圣弟子,他已入于法流并培育戒随念。
“再者,摩诃男,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他自己的布施:‘我实为获益,我实为善得,在为悭吝之垢所困扰的众生中,我住于家中,心离悭吝之垢,自由布施,伸手助人,乐于舍离,致力于慈善,乐于施与及分享。’当一位圣弟子如此忆念他自己的布施时,在那一刻,他的心不被贪、瞋、痴所困扰;他的心是正直的,以布施为所缘……。这被称为一位在不平等的众生中平等安住,在有苦恼的众生中无苦恼安住的圣弟子,他已入于法流并培育舍随念。
“再者,摩诃男,一位圣弟子如此培育天随念:‘有天人在各天界。24我身中亦有此等信、戒、闻、舍、慧,彼等天人因拥有此等特质,故从此处死后,得生于彼处。’当一位圣弟子忆念他自己的信、戒、闻、舍、慧,以及天人们的信、戒、闻、舍、慧时,在那一刻,他的心不被贪、瞋、痴所困扰;他的心是正直的,以天人为所缘……。这被称为一位在不平等的众生中平等安住,在有苦恼的众生中无苦恼安住的圣弟子,他已入于法流并培育天随念。
“摩诃男,一位已证得圣果、了悟教法的圣弟子,常如此这般地安住。”
(AN 6:10; III 284–88)
第八篇:四念住
1. 如是我闻。一时,世尊住在俱卢国(Kuru),一个名叫甘马萨昙马(Kammāsadhamma)的俱卢人城镇。在那里,他对诸比丘说:“诸比丘。”——“尊者。”他们回答道。世尊如此说道:
2. “诸比丘,这是唯一的道路25,为了众生的清净,为了超越愁与悲,为了灭除苦与忧,为了证得正道,为了实现涅槃——那就是四念住。
3. “是哪四种?于此,诸比丘,一位比丘于身随观身而住,热忱、正知、具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26他于受随观受而住,热忱、正知、具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他于心随观心而住,热忱、正知、具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他于法随观法而住,热忱、正知、具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欲与忧恼。27
[身随观念住]
[1. 出入息念]
4. “诸比丘,一位比丘如何于身随观身而住?于此,一位比丘去到森林、树下或空屋,他结跏趺坐,保持身体正直,将念安住于面前,只是具念地入息,具念地出息。入息长,他了知:‘我入息长’;或出息长,他了知:‘我出息长。’入息短,他了知:‘我入息短’;或出息短,他了知:‘我出息短。’28他如此修学:‘我将觉知全身而入息’;他如此修学:‘我将觉知全身而出息。’29他如此修学:‘我将平息身行而入息’;他如此修学:‘我将平息身行而出息。’30就像一位熟练的车床工或他的学徒,在做一个长转时,了知:‘我做一个长转’;或者在做一个短转时,了知:‘我做一个短转’;同样地,入息长,一位比丘了知:‘我入息长’……他如此修学:‘我将平息身行而出息。’
5. “如此,他于内随观身而住,或于外随观身而住,或于内外随观身而住。31或者,他随观身中生起的性质而住,或随观身中坏灭的性质而住,或随观身中生起与坏灭的性质而住。32或者,‘有身’之念,仅为纯粹的了知与一再的忆念所需,而单纯地在他心中建立起来。并且他独立而住,不执取世间任何事物。这就是一位比丘于身随观身而住的方式。
[2. 四威仪]
6. “再者,诸比丘,行走时,一位比丘了知:‘我正在行走’;站立时,他了知:‘我正在站立’;坐着时,他了知:‘我正在坐着’;躺下时,他了知:‘我正在躺下’;或者,无论他的身体处于何种姿势,他都如实了知。33
7. “如此,他于内、于外、于内外随观身而住……并且他独立而住,不执取世间任何事物。那也是一位比丘于身随观身而住的方式。
[3. 正知]
8. “再者,诸比丘,一位比丘在前行与返回时,是具足正知而行;34在向前看与向旁看时,是具足正知而行;在屈伸肢体时,是具足正知而行;在穿衣及持外衣与钵时,是具足正知而行;在食、饮、嚼、尝时,是具足正知而行;在大小便时,是具足正知而行;在行、住、坐、卧、醒、语、默时,是具足正知而行。
9. “如此,他于内、于外、于内外随观身而住……并且他独立而住,不执取世间任何事物。那也是一位比丘于身随观身而住的方式。
[4. 身不净观]
10. “再者,诸比丘,一位比丘审视此身,从脚底向上,从头顶向下,以皮肤为界,充满种种不净之物,如此思惟:‘此身中有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骨髓、肾、心、肝、肋膜、脾、肺、肠、肠膜、胃、粪、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油脂、唾、涕、关节滑液、尿。’35就像一个两端开口的袋子,装满了各种谷物,如山稻、红米、豆、豌豆、小米和白米,一个视力良好的人打开它,如此审视:‘这是山稻,这是红米,这些是豆,这些是豌豆,这是小米,这是白米’;同样地,一位比丘审视此身……充满种种不净之物,如此思惟:‘此身中有发……及尿。’
11. “如此,他于内、于外、于内外随观身而住……并且他独立而住,不执取世间任何事物。那也是一位比丘于身随观身而住的方式。
[5. 诸界]
12. “再者,诸比丘,一位比丘审视此身,无论其如何放置、如何处置,皆由诸界组成,如此思惟:‘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36就像一位熟练的屠夫或他的学徒,宰杀了一头牛后,坐在十字路口,把它切成块;同样地,一位比丘审视此身……由诸界组成,如此思惟:‘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
13. “如此,他于内、于外、于内外随观身而住……并且他独立而住,不执取世间任何事物。那也是一位比丘于身随观身而住的方式。
[6–14. 九种墓地观]
14. “再者,诸比丘,犹如他看见一具被弃置于墓地的尸体,死后一、二或三日,肿胀、青瘀、流脓,一位比丘以此与自身作比较:‘此身亦是如此的性质,将会变成那样,无法幸免于此命运。’37
15. “如此,他于内、于外、于内外随观身而住……并且他独立而住,不执取世间任何事物。那也是一位比丘于身随观身而住的方式。
16. “再者,犹如他看见一具被弃置于墓地的尸体,正被乌鸦、鹰、秃鹫、狗、豺狼或各种虫类所吞食,一位比丘以此与自身作比较:‘此身亦是如此的性质,将会变成那样,无法幸免于此命运。’
17. “……那也是一位比丘于身随观身而住的方式。
18–24. “再者,犹如他看见一具被弃置于墓地的尸体,一具带血肉、由筋腱连接的骸骨……一具无肉、染血、由筋腱连接的骸骨……一具无血肉、由筋腱连接的骸骨……散落各处的骨头——这里是手骨,那里是脚骨,这里是胫骨,那里是大腿骨,这里是髋骨,那里是脊骨,这里是头骨——一位比丘以此与自身作比较:‘此身亦是如此的性质,将会变成那样,无法幸免于此命运。’38
25. “……那也是一位比丘于身随观身而住的方式。
26–30. “再者,犹如他看见一具被弃置于墓地的尸体,骨头已白如贝壳……骨头堆积……超过一年的骨头,腐烂成尘,一位比丘以此与自身作比较:‘此身亦是如此的性质,将会变成那样,无法幸免于此命运。’
31. “如此,他于内随观身而住,或于外随观身而住,或于内外随观身而住。或者,他随观身中生起的性质而住,或随观身中坏灭的性质而住,或随观身中生起与坏灭的性质而住。或者,‘有身’之念,仅为纯粹的了知与一再的忆念所需,而单纯地在他心中建立起来。并且他独立而住,不执取世间任何事物。那也是一位比丘于身随观身而住的方式。
[受随观念住]
32. “诸比丘,一位比丘如何于受随观受而住?39于此,当感到乐受时,一位比丘了知:‘我感到乐受’;当感到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到苦受’;当感到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不苦不乐受。’当感到肉体的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肉体的乐受’;当感到精神的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精神的乐受’;当感到肉体的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到肉体的苦受’;当感到精神的苦受时,他了知:‘我感到精神的苦受’;当感到肉体的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肉体的不苦不乐受’;当感到精神的不苦不乐受时,他了知:‘我感到精神的不苦不乐受。’
33. “如此,他于内随观受而住,或于外随观受而住,或于内外随观受而住。或者,他随观受中生起的性质而住,或随观受中坏灭的性质而住,或随观受中生起与坏灭的性质而住。40或者,‘有受’之念,仅为纯粹的了知与一再的忆念所需,而单纯地在他心中建立起来。并且他独立而住,不执取世间任何事物。这就是一位比丘于受随观受而住的方式。
[心随观念住]
34. “诸比丘,一位比丘如何于心随观心而住?41于此,一位比丘了知有贪的心为有贪的心,无贪的心为无贪的心。他了知有瞋的心为有瞋的心,无瞋的心为无瞋的心。他了知有痴的心为有痴的心,无痴的心为无痴的心。他了知收缩的心为收缩的心,散乱的心为散乱的心。他了知广大的心为广大的心,不广大的心为不广大的心。他了知有上的心为有上的心,无上的心为无上的心。他了知得定的心为得定的心,未得定的心为未得定的心。他了知解脱的心为解脱的心,未解脱的心为未解脱的心。42
35. “如此,他于内随观心而住,或于外随观心而住,或于内外随观心而住。或者,他随观心中生起的性质而住,或随观心中坏灭的性质而住,或随观心中生起与坏灭的性质而住。43或者,‘有心’之念,仅为纯粹的了知与一再的忆念所需,而单纯地在他心中建立起来。并且他独立而住,不执取世间任何事物。这就是一位比丘于心随观心而住的方式。
[法随观念住]
[1. 五盖]
36. “诸比丘,比丘如何就法观法而住?于此,比丘就五盖观法而住。44比丘如何就五盖观法而住?于此,当他内心有欲贪时,比丘了知:‘我内心有欲贪’;或者当他内心没有欲贪时,他了知:‘我内心没有欲贪’;并且他也了知未生起的欲贪如何生起,已生起的欲贪如何被断除,以及被断除的欲贪未来如何不再生起。”45 “当他内心有瞋恚时……当他内心有昏沉与睡眠时……当他内心有掉举与追悔时……当他内心有疑时,比丘了知:‘我内心有疑’;或者当他内心没有疑时,他了知:‘我内心没有疑’;并且他也了知未生起的疑如何生起,已生起的疑如何被断除,以及被断除的疑未来如何不再生起。
37. “如此,他就法于内观法而住,或就法于外观法而住,或就法于内、外观法而住。或者,他于法中观察其生起之性而住,或于法中观察其灭去之性而住,或于法中观察其生起与灭去之性而住。或者,只是为了单纯的知和持续的正念,他心中确立起‘有法’之念。他独立地安住,不执取世间的任何事物。这就是比丘就五盖观法而住的方式。
[2. 五蕴]
38. “再者,诸比丘,比丘就五取蕴观法而住。46比丘如何就五取蕴观法而住?于此,比丘了知:‘色是如此,其集起是如此,其灭去是如此;受是如此,其集起是如此,其灭去是如此;想是如此,其集起是如此,其灭去是如此;诸行是如此,其集起是如此,其灭去是如此;识是如此,其集起是如此,其灭去是如此。’”47
39. “如此,他就法于内、于外、于内外而观法而住。……他独立地安住,不执取世间的任何事物。这就是比丘就五取蕴观法而住的方式。
[3. 六根]
40. “再者,诸比丘,比丘就六内外处观法而住。48比丘如何就六内外处观法而住?于此,比丘了知眼,了知色,也了知缘此二者而生起的结;并且他也了知未生起的结如何生起,已生起的结如何被断除,以及被断除的结未来如何不再生起。49
“他了知耳,了知声……他了知鼻,了知香……他了知舌,了知味……他了知身,了知触……他了知意,了知法,也了知缘此二者而生起的结;并且他也了知未生起的结如何生起,已生起的结如何被断除,以及被断除的结未来如何不再生起。
41. “如此,他就法于内、于外、于内外而观法而住。……他独立地安住,不执取世间的任何事物。这就是比丘就六内外处观法而住的方式。
[4. 七觉支]
42. “再者,诸比丘,比丘就七觉支观法而住。50比丘如何就七觉支观法而住?于此,当他内心有念觉支时,比丘了知:‘我内心有念觉支’;或者当他内心没有念觉支时,他了知:‘我内心没有念觉支’;并且他也了知未生起的念觉支如何生起,以及已生起的念觉支如何通过培育而圆满。
“当他内心有择法觉支时……当他内心有精进觉支时……当他内心有喜觉支时……当他内心有轻安觉支时……当他内心有定觉支时……当他内心有舍觉支时,比丘了知:‘我内心有舍觉支’;或者当他内心没有舍觉支时,他了知:‘我内心没有舍觉支’;并且他也了知未生起的舍觉支如何生起,以及已生起的舍觉支如何通过培育而圆满。51
43. “如此,他就法于内、于外、于内外而观法而住。……他独立地安住,不执取世间的任何事物。这就是比丘就七觉支观法而住的方式。
[5. 四圣谛]
44. “再者,诸比丘,比丘就四圣谛观法而住。52比丘如何就四圣谛观法而住?于此,比丘如实了知:‘此是苦。此是苦集。此是苦灭。此是导向苦灭之道。’
45. “如此,他就法于内观法而住,或就法于外观法而住,或就法于内、外观法而住。或者,他于法中观察其生起之性而住,或于法中观察其灭去之性而住,或于法中观察其生起与灭去之性而住。或者,只是为了单纯的知和持续的正念,他心中确立起‘有法’之念。他独立地安住,不执取世间的任何事物。这就是比丘就四圣谛观法而住的方式。
[结论]
46. “诸比丘,若任何人如此培育此四念住达七年,可预期他获得两种果位之一:或于现法中得究竟知,或若有执取之余,则为不还者。53
“诸比丘,莫说七年。若任何人如此培育此四念住达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二年……一年,可预期他获得两种果位之一:或于现法中得究竟知,或若有执取之余,则为不还者。
“诸比丘,莫说一年。若任何人如此培育此四念住达七个月……六个月……五个月……四个月……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半个月,可预期他获得两种果位之一:或于现法中得究竟知,或若有执取之余,则为不还者。
“诸比丘,莫说半个月。若任何人如此培育此四念住达七日,可预期他获得两种果位之一:或于现法中得究竟知,或若有执取之余,则为不还者。
47. “因此,经中如是说:‘诸比丘,此乃净化众生、超越愁悲、灭除苦忧、证得正道、亲证涅槃的唯一之道——即四念住。’”
此为世尊所说。诸比丘心满意足,欢喜世尊所说。
(MN 10: Satipaṭṭhāna Sutta; I 55–63)
第九篇:入出息念
于舍卫城 (Sāvatthī),尊者阿难 (Ānanda) 走近世尊,向他行礼后,坐于一旁说道:“尊者,是否有一法,当被培育与修习时,能圆满四法?是否有四法,当被培育与修习时,能圆满七法?是否有七法,当被培育与修习时,能圆满二法?”
“阿难 (Ānanda),确实有一法,当被培育与修习时,能圆满四法;有四法,当被培育与修习时,能圆满七法;有七法,当被培育与修习时,能圆满二法。”
“可是,尊者,是哪一法,当被培育与修习时,能圆满四法;又是哪四法,当被培育与修习时,能圆满七法;又是哪七法,当被培育与修习时,能圆满二法?”
“阿难 (Ānanda),入出息念定即是那一法,当被培育与修习时,能圆满四念住。四念住,当被培育与修习时,能圆满七觉支。七觉支,当被培育与修习时,能圆满明与解脱。
(1)圆满四念住
“阿难 (Ānanda),入出息念定如何被培育与修习,从而圆满四念住?于此,阿难 (Ānanda),比丘去到森林、树下或空寂处,坐下。54他结跏趺坐,端正身体,将念安立于面前,正念地入息,正念地出息。“入息长,他知道:‘我入息长’;或出息长,他知道:‘我出息长’。入息短,他知道:‘我入息短’;或出息短,他知道:‘我出息短’。他如此训练:‘感受全身,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感受全身,我将出息’。他如此训练:‘平静身行,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平静身行,我将出息’。
“他如此训练:‘感受喜,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感受喜,我将出息’。他如此训练:‘感受乐,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感受乐,我将出息’。他如此训练:‘感受心行,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感受心行,我将出息’。他如此训练:‘平静心行,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平静心行,我将出息’。55
“他如此训练:‘感受心,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感受心,我将出息’。他如此训练:‘令心喜悦,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令心喜悦,我将出息’。他如此训练:‘令心入定,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令心入定,我将出息’。他如此训练:‘令心解脱,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令心解脱,我将出息’。56
“他如此训练:‘随观无常,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随观无常,我将出息’。他如此训练:‘随观离贪,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随观离贪,我将出息’。他如此训练:‘随观灭尽,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随观灭尽,我将出息’。他如此训练:‘随观舍遣,我将入息’;他如此训练:‘随观舍遣,我将出息’。57
“阿难 (Ānanda),每当比丘入息长时,知道:‘我入息长’……[如上]……当他如此训练:‘平静身行,我将出息’时——于此际,该比丘住于观身中的身,热忱、正知、正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爱与忧恼。为何如此?阿难 (Ānanda),我说这是身中的一种身,即入息与出息。因此,阿难 (Ānanda),于此际,该比丘住于观身中的身,热忱、正知、正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爱与忧恼。
“阿难 (Ānanda),每当比丘如此训练:‘感受喜,我将入息’……当他如此训练:‘平静心行,我将出息’时——于此际,该比丘住于观受中的受,热忱、正知、正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爱与忧恼。为何如此?阿难 (Ānanda),我说这是受中的一种受,即对入息与出息的密切作意。58因此,阿难 (Ānanda),于此际,该比丘住于观受中的受,热忱、正知、正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爱与忧恼。
“阿难 (Ānanda),每当比丘如此训练:‘感受心,我将入息’……当他如此训练:‘令心解脱,我将出息’时——于此际,该比丘住于观心中心,热忱、正知、正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爱与忧恼。为何如此?阿难 (Ānanda),我说,对于一个糊涂且缺乏正知的人,不可能培育入出息念定。因此,阿难 (Ānanda),于此际,该比丘住于观心中心,热忱、正知、正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爱与忧恼。
“阿难 (Ānanda),每当比丘如此训练:‘随观无常,我将入息’……当他如此训练:‘随观舍遣,我将出息’时——于此际,该比丘住于观法中的法,热忱、正知、正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爱与忧恼。以智慧见到贪爱与忧恼的舍离,他成为一位以舍心密切旁观者。59因此,阿难 (Ānanda),于此际,该比丘住于观法中的法,热忱、正知、正念,已调伏对世间的贪爱与忧恼。
“阿难 (Ānanda),当入出息念定被如此培育与修习时,它即圆满四念住。
(2)圆满七觉支
“阿难 (Ānanda),四念住如何被培育与修习,从而圆满七觉支?
“阿难 (Ānanda),每当比丘住于观身中的身时,于此际,不混乱的正念即于该比丘心中确立。阿难 (Ānanda),每当不混乱的正念已于比丘心中确立时,于此际,念觉支即被该比丘所激发;于此际,该比丘培育念觉支;于此际,念觉支于该比丘心中通过培育而达圆满。60
“如此正念地安住,他以智慧辨识、审察、探究该法。阿难 (Ānanda),每当比丘如此正念地安住,以智慧辨识、审察、探究该法时,于此际,择法觉支61即被该比丘所激发;于此际,该比丘培育择法觉支;于此际,择法觉支于该比丘心中通过培育而达圆满。
“当他以智慧辨识、审察、探究该法时,他的精进即不松懈地被激发。阿难 (Ānanda),每当比丘在以智慧辨识、审察、探究该法时,其精进不松懈地被激发,于此际,精进觉支即被该比丘所激发;于此际,该比丘培育精进觉支;于此际,精进觉支于该比丘心中通过培育而达圆满。
“当他的精进被激发时,他心中即生起喜。阿难 (Ānanda),每当精进被激发的比丘心中生起喜时,于此际,喜觉支即被该比丘所激发;于此际,该比丘培育喜觉支;于此际,喜觉支于该比丘心中通过培育而达圆满。
“对于一个心为喜所提升的人,其身变得轻安,其心也变得轻安。阿难 (Ānanda),每当心为喜所提升的比丘身变得轻安、心变得轻安时,于此际,轻安觉支即被该比丘所激发;于此际,该比丘培育轻安觉支;于此际,轻安觉支于该比丘心中通过培育而达圆满。
“对于一个身轻安且快乐的人,其心变得专注。阿难 (Ānanda),每当身轻安且快乐的比丘心变得专注时,于此际,定觉支即被该比丘所激发;于此际,该比丘培育定觉支;于此际,定觉支于该比丘心中通过培育而达圆满。
“他成为一位以舍心密切旁观如此专注之心的人。阿难 (Ānanda),每当比丘成为一位以舍心密切旁观如此专注之心的人时,于此际,舍觉支即被该比丘所激发;于此际,该比丘培育舍觉支;于此际,舍觉支于该比丘心中通过培育而达圆满。
“阿难 (Ānanda),每当比丘住于观受中的受……心中心……法中的法时,于此际,不混乱的正念即于该比丘心中确立。阿难 (Ānanda),每当不混乱的正念已于比丘心中确立时,于此际,念觉支即被该比丘所激发;于此际,该比丘培育念觉支;于此际,念觉支于该比丘心中通过培育而达圆满。
[一切皆应如第一念住之情形详述。]
“他成为一位以舍心密切旁观如此专注之心的人。阿难 (Ānanda),每当比丘成为一位以舍心密切旁观如此专注之心的人时,于此际,舍觉支即被该比丘所激发;于此际,该比丘培育舍觉支;于此际,舍觉支于该比丘心中通过培育而达圆满。
“阿难 (Ānanda),当四念住被如此培育与修习时,它们即圆满七觉支。
(3)圆满明与解脱
“阿难 (Ānanda),七觉支如何被培育与修习,从而圆满明与解脱?
“于此,阿难 (Ānanda),比丘培育念觉支,此觉支依止远离、离贪、灭尽,导向舍遣。他培育择法觉支……精进觉支……喜觉支……轻安觉支……定觉支……舍觉支,此觉支依止远离、离贪、灭尽,导向舍遣。
“阿难 (Ānanda),当七觉支被如此培育与修习时,它们即圆满明与解脱。”
(SN 54:13; V 328–33 ≠ MN 118.15–43; III 82–88)
第十篇:掌控的成就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 (Sāriputta) 住在舍卫城 (Sāvatthī) 的
祇树给孤独园 (Jeta’s Grove, Anāthapiṇḍika’s Park)。62一日晨,他穿好衣,持衣钵,进入舍卫城 (Sāvatthī) 乞食。在舍卫城 (Sāvatthī) 乞食完毕,饭后从乞食归来,他前往盲人林作日间住。他深入盲人林,坐于一棵树下作日间住。
到了傍晚,尊者舍利弗 (Sāriputta) 从独处中出来,前往祇树给孤独园 (Jeta’s Grove, Anāthapiṇḍika’s Park)。尊者阿难 (Ānanda) 从远处看见他走来,便对他说:“舍利弗 (Sāriputta) 道友,您的诸根清明,面色纯净、明亮。您今日安住于何处?”
“道友,于此,我远离诸欲,远离诸不善法,进入并安住于初禅,此禅寻、伺俱在,有由远离所生的喜与乐。然而,道友,我并未生起‘我正在证入初禅’、‘我已证得初禅’或‘我已从初禅出定’这样的念头。”
“这必定是因为您心中我作、我所作以及我慢的潜在倾向已被彻底根除许久,所以才没有生起那样的念头。”63
[另一次,尊者舍利弗 (Sāriputta) 说:] “于此,道友,随着寻、伺的平息,我进入并安住于第二禅,此禅有内在的净信与心的一境性,无寻、无伺,有由定所生的喜与乐。然而,道友,我并未生起‘我正在证入第二禅’、‘我已证得第二禅’或‘我已从第二禅出定’这样的念头。”
“这必定是因为您心中我作、我所作以及我慢的潜在倾向已被彻底根除许久,所以才没有生起那样的念头。”
[另一次,尊者舍利弗 (Sāriputta) 说:] “于此,道友,随着喜的消退,我住于舍,正念、正知,以身感受乐;我进入并安住于第三禅,圣者们宣说:‘此为舍、念、乐住。’然而,道友,我并未生起‘我正在证入第三禅……’”[如上文补全。]
[另一次,尊者舍利弗 (Sāriputta) 说:] “于此,道友,随着舍乐、舍苦,以及先前喜、忧的灭没,我进入并安住于第四禅,此禅不苦不乐,由舍而念清净。然而,道友,我并未生起‘我正在证入第四禅……’”
[另一次,尊者舍利弗 (Sāriputta) 说:] “于此,道友,通过完全超越色想,随着有对想的灭没,不作意种种想,了知‘空是无边的’,我进入并安住于空无边处定。然而,道友,我并未生起‘我正在证入空无边处定……’”
[另一次,尊者舍利弗 (Sāriputta) 说:] “于此,道友,通过完全超越空无边处定,了知‘识是无边的’,我进入并安住于识无边处定。然而,道友,我并未生起‘我正在证入识无边处定……’”
[另一次,尊者舍利弗 (Sāriputta) 说:] “于此,道友,通过完全超越识无边处定,了知‘无所有’,我进入并安住于无所有处定。然而,道友,我并未生起‘我正在证入无所有处定……’”
[另一次,尊者舍利弗 (Sāriputta) 说:] “于此,道友,通过完全超越无所有处定,我进入并安住于非想非非想处定。然而,道友,我并未生起‘我正在证入非想非非想处定……’”
[另一次,尊者舍利弗 (Sāriputta) 说:] “于此,道友,通过完全超越非想非非想处定,我进入并安住于想受灭尽定。然而,道友,我并未生起‘我正在证入想受灭尽定’、‘我已证得想受灭尽定’或‘我已从想受灭尽定出定’这样的念头。”64
“这必定是因为您心中我作、我所作以及我慢的潜在倾向已被彻底根除许久,所以才没有生起那样的念头。”
(SN 28:1–9, combined; III 235–38)
注释
-
这些是入流、一来、不还和阿罗汉的阶段。见第十章。 ↩
-
见,例如,AN 9:3 (IV 358) = Ud 4:1。 ↩
-
该经的译文及其义注和副义注的大量摘录可见于索玛长老 (Soma Thera) 的《念住之道》(The Way of Mindfulness)。两部优秀的现代阐释,也包括该经的译文,分别是:向智长老 (Nyanaponika Thera) 的《佛教禅修的核心》(The Heart of Buddhist Meditation),以及无着比丘 (Anālayo) 的《念住:直达证悟之道》(Satipaṭṭhāna: The Direct Path to Realization)。 ↩
-
Mp:当止独立于观而培育时,它能导致对五盖的抑制,其中第一个是欲欲,并最终达到禅那 (jhānas) 的“增上心” (adhicitta),其特征是无欲。但只有当止与观结合培育时,它才能生起圣道,从而根除欲欲的潜在倾向(通过不还道)和对有的执着(通过阿罗汉道)。Mp 在此将止解释为第二种意义,大概是根据经文的最后一句。 ↩
-
Mp:培育的是出世间道的智慧 (magga-paññā)。“舍断的无明”是轮回根源处的大无明。 ↩
-
阿罗汉果常被描述为“无漏心解脱、慧解脱” (anāsava-cetovimutti-paññāvimutti)。Mp 解释“心解脱” (cetovimutti) 是与(阿罗汉)果相关的定,“慧解脱” (paññāvimutti) 是与果相关的慧。Mp 指的是“阿罗汉果定” (arahattaphala-samāpatti),这是一种出世间的禅定,阿罗汉在其中体验涅槃 (Nibbāna) 的寂静之乐。 ↩
-
Samathapubbaṅgamaṃ vipassanaṃ。 Mp:“这是指禅修者先获得奢摩他,然后再修习毗婆舍那。” 义注师称这样的禅修者为奢摩他行者 (samathayānika)。见 Vism 587; Ppn 18:3。 ↩
-
“道” (magga) 是第一个出世间道,即入流道。根据 Mp, “培育该道”意味着为证得更高的三道而修行。关于十结,见第374–75页;关于七随眠,见第426页(第一章,注5)。 ↩
-
Vipassanāpubbaṅgamaṃ samathaṃ。 Mp:“这是指天生倾向于先证得毗婆舍那,然后基于毗婆舍那生起定的人。” 在义注文献中,这被称为毗婆舍那行者 (vipassanāyānika)。见 Vism 588; Ppn 18:4。 ↩
-
Samathavipassanaṃ yuganaddhaṃ。在这种修行模式中,一个人进入初禅那,出定后,对此体验应用观,即,他视禅那的五蕴(色、受、想等)为无常、苦、无我。然后他进入第二禅那并以观来审察它。他对其他禅那也应用相同的程序,直到证得入流道等。 ↩
-
Dhammuddhaccaviggahitaṃ mānasaṃ hoti。 Mp 说,此处的“掉举” (uddhacca) 是对十种“观染” (vipassanūpakkilesa) 的反应,人们误将这些观染视为证道的标志。(关于观染,见 Vism 633–38; Ppn 20:105–28。)然而,“法掉举”也可能是由渴望证悟法而引起的心理困扰。这种精神焦虑状态,当突然解决时,有时会促发瞬间的觉醒体验。例如,见 Ud 1:10 中婆酰·陀卢支离 (Bāhiya Dārucīriya) 的故事。 ↩
-
Mp 解释内心的止 (ajjhattaṃ cetosamatha) 是指安止定(即禅那),而增上慧法毗婆舍那 (adhipaññādhammavipassanā) 是指辨别诸行的观智 (saṅkhārapariggāhaka-vipassanāñāṇa)。 ↩
-
“行” (saṅkhārā) 是构成五蕴的有为法。关于五蕴,见正文 第九章第四篇(1)(a)-(e)。 ↩
-
Spk 将论藏中三种出离 (nissaraṇa) 的区别应用于每个盖。通过禅那 (jhāna) 以镇伏的方式出离盖 (vikkhambhananissaraṇa);通过观以彼分的方式出离 (tadaṅganissaraṇa);通过出世间道以断除的方式出离 (samucchedanissaraṇa)。因此:(1) 欲欲通过基于身体不净观(asubha;见正文 第八章第八篇(10))的初禅那被镇伏,并通过阿罗汉道被根除(因为此处的 kāmacchanda 被广泛地解释为包括对任何对象的欲望,而不仅是感官欲望);(2) 瞋恚通过基于慈心的初禅那被镇伏,并通过不还道被根除;(3) 昏沉和睡眠通过光明想(即观想明亮的光,如日轮或满月)被镇伏,并通过阿罗汉道被根除;(4) 掉举和追悔通过奢摩他被镇伏,追悔通过不还道被根除,掉举通过阿罗汉道被根除;(5) 疑通过辨别诸法 (dhammavavatthāna;见 Vism 587–89; Ppn 18:3–8) 被镇伏,并通过入流道被根除。 ↩
-
这三种是“邪思惟”,与八正道的第二支正思惟或正志相反。见正文 第七章第二篇。 ↩
-
Dhammavitakka。 Mp 认为这是指十种“观染”,但更自然的理解是,这仅仅指对法的强迫性思惟。 ↩
-
这是指六神通 (abhiññā) 的前提条件,下文将予以描述。五种世间神通的前提条件是第四禅那 (jhāna)。第六种神通——阿罗汉果的前提条件是观。唯有此神通是出世间的。 ↩
-
Ps 说,增上心 (adhicitta) 是指作为观禅基础的八定的心;它被称为“增上心”,因为它高于十善业道中的普通(善)心。五种“相” (nimitta) 可以理解为去除散乱念头的实用方法。只有当散乱变得持续或突兀时才应使用它们;其他时候,禅修者应保持在主要的禅修所缘上。 ↩
-
Ps:当对有情生起欲欲的念头时,“其他的相”是修习身体的不净观(见正文 第八章第八篇(10));当念头指向无情物时,“其他的相”是作意无常。当对有情生起瞋恨的念头时,“其他的相”是修习慈心;当念头指向无情物时,“其他的相”是作意界(见正文 第八章第八篇(12))。对治与痴相关的念头的方法是依止老师生活、学习法、探究其义、听闻法以及探究因缘。 ↩
-
Vitakka-saṅkhāra-sanṭhānaṃ。 Ps 将此处的 saṅkhāra 解释为条件、原因或根源,并将该复合词解释为“停止念头的原因”。这是通过在不善念头生起时追问:“它的原因是什么?它原因的原因是什么?”等方式来完成的。这样的追问会减慢并最终切断不善念头的流动。 ↩
-
Tadārammaṇaṃ,字面意思是“以那个(一)为所缘”。Ps:首先对以五种妄语中的任何一种对自己说话的人培育慈心,然后将那份慈心导向一切众生,使整个世界成为所缘。 ↩
-
摩诃男 (Mahānāma) 是佛陀的近亲,释迦族的重要成员。 ↩
-
“证果” (āgataphala) 和“解法” (viññātasāsana) 这两个短语表明,他问的是至少是入流者级别的圣弟子的禅修。然而,这类禅修对任何水平的人来说都是有益的,因为它们能暂时净化心的烦恼并导向定。 ↩
-
我节略了此处的原文,原文列举了不同的天界。 ↩
-
巴利语为 ekāyano ayaṃ bhikkhave maggo。几乎所有的翻译者都将此句理解为宣称四念住 (satipaṭṭhāna) 是一条唯一的道路。因此,索玛长老 (Soma Thera) 将其译为:“比丘们,这是唯一之道”,向智长老 (Nyanaponika Thera) 将其译为:“诸比丘,此乃唯一之道。”然而,在 MN 12.37–42 中,ekāyana magga 的明确含义是“一条只朝一个方向走的路”,这似乎也最符合此处的语境。其要点似乎只是说,四念住只有一个方向,即朝向“众生的清净……涅槃的证悟”。 ↩
-
Ps 说,重复“于身随观身” (kāye kāyānupassī) 的目的是为了精确地确定观照的所缘,并将该所缘与其他可能混淆的所缘区分开来。因此,在这种修行中,应当如其本然地观照身体,而不是观照自己对身体的感受、想法和情绪。这句话也意味着,身体应当仅仅被观照为身体,而不是男人、女人、自我或一个众生。类似的考量也适用于其他三个念住的重复句。“贪与忧” (abhijjhā-domanassaṃ),根据 Ps 的说法,意味着欲欲和瞋恚,是五盖中的主要部分。 ↩
-
关于接下来要讨论的经文结构,见第262–63页。 ↩
-
修习安那般那念 (ānāpānasati) 并不像哈达瑜伽那样刻意地调节呼吸,而是努力将觉知持续地专注于以自然节奏出入的呼吸上。正念被建立在鼻孔或上唇,任何最能清晰感觉到呼吸冲击的地方。呼吸的长短被注意到,但不是有意识地控制。这种禅修业处的完整培育方法在正文 第八章第九篇中有解释。根据义注体系对安那般那念的详细解释见 Vism 266–93; Ppn 8:145–244。亦可见髻智长老 (Ñāṇamoli) 翻译的文本集《安那般那念》。 ↩
-
Ps,与其他巴利义注一致,解释“觉知全身” (sabbakāyapaṭisaṃvedī) 意指禅修者通过其开始、中间和结束三个阶段,觉知到每一个入息和出息。这个解释很难与原文的字面意思相符,原文最初可能只是意指对整个身体的整体觉知。也很难理解 -paṭisaṃvedī 如何能意为“觉知到”;这个后缀基于动词 paṭisaṃvedeti,意为“体验”或“感受”,其细微差别与“觉知”不同。 ↩
-
“身行” (kāyasaṅkhāra) 在 MN 44.13 (I 301) 和 SN 41:6 (IV 293) 中被定义为入出息。因此,如 Ps 所解释,随着这项修行的成功培育,禅修者的呼吸会变得越来越宁静、安详与平和。 ↩
-
Ps:“于内”:观照自己身体内的呼吸。“于外”:观照在他人身体内发生的呼吸。“于内于外”:交替地、不间断地观照自己身体内和他人身体内的呼吸。类似的解释适用于每个其他部分之后的重复句,只是在观受、观心和观法时,除非拥有他心通,否则于外的观照必须是推断性的。对于没有他心通的人来说,除了观察胸部的起伏,直接观照他人的呼吸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观照也必须是推断性的。 ↩
-
Ps义注解释说,身的“生起性质”(samudayadhamma)可以通过其以无明、爱、业和食为条件的缘起,以及身中物质现象的刹那生起来观察。在安般念的情况下,一个额外的条件是呼吸的生理机制。身的“坏灭性质”(vayadhamma)则体现在其缘的止息而导致身现象的止息,以及身现象的刹那坏灭中。 ↩
-
此练习中提到的对威仪的理解,并非我们对身体活动的通常认知,而是在每一种姿势下对身体的紧密、持续和仔细的觉知,并结合分析性的审察,旨在破除有一个“我”作为身体运动主体的错觉。 ↩
-
正知(Sampajañña),在义注中被分析为四种类型:(1) 对行为目的之正知;(2) 对实现目的之方法的适宜性之正知;(3) 对行境之正知,即在日常活动中不离禅修所缘;以及(4) 对实相之正知,即觉知在个人活动背后并无一个恒常的我。参见Soma,《念住之道》,第60–100页;Nyanaponika,《佛教禅修之心》,第46–55页。 ↩
-
根据义注的方法,对此修习的详细解释见《清净道论》239–266;Ppn 8:42–144。肠系膜是连接小肠至腹壁后侧的组织褶皱。 ↩
-
此四界是物质的主要属性——地界(pathavīdhātu)是坚实性;水界(āpodhātu)是内聚性;火界(tejodhātu)是热量;以及风界(vāyodhātu)是压力或膨胀。关于四界作意的更详细说明,见第九篇,4(3)(c)。关于义注的解释,见《清净道论》347–72;Ppn 11:27–126。 ↩
-
“如同”(seyyathāpi)这个词组表明,这项禅修以及接下来的禅修,不必基于对腐烂尸体的实际观察,也可以通过想象来进行。“此身”,当然指的是禅修者自己的身体。 ↩
-
这里提到的四种尸体,以及下面提到的三种,每一种都可以作为独立且自足的禅修所缘;或者整套可以作为一个渐进的系列,用以在心中铭印身体无常和无实质的观念。这一进程在§§26–30中继续。 ↩
-
受(vedanā)指经验的情感特质,包括身体和心理的,可以是乐、苦或不苦不乐,即舍受。关于这些受的“世俗”和“出世”种类的例子,在《中部》137.9–15 (III 217–19)中,分别以基于居家生活和出离的六种喜、忧和舍的名目下给出。 ↩
-
受的生起和坏灭的条件与身的条件相同(见第442页(第八章,注32)),只是食被触所取代,因为触是受的条件。 ↩
-
心(citta)作为禅修的所缘,指的是意识的总体状态和水平。由于意识本身只是对所缘的纯粹了知或认知,任何心识状态的性质都由其相应的心所决定,例如贪、嗔、痴或其对立面。 ↩
-
此段落中给出的心的例子,对比了善与不善,或已培育与未培育的心识状态。然而,“昏沉”与“散乱”这一对则由不善的对立面构成,前者源于迟钝和睡意,后者源于掉举和追悔。Ps义注解释“广大心”和“无上心”为与禅那及无色界定相应的禅定之心,“非广大心”和“有上心”为与欲界意识相应之心。义注说“解脱心”应理解为通过观禅或禅那而暂时、部分地从烦恼中解脱的心。由于四念住的修习属于道的初步阶段,义注认为这最后一类不应理解为通过证得超世间道而解脱的心;然而,这种解释或许不应被排除。 ↩
-
心的生起和坏灭的条件与身的条件相同,只是食被名色所取代,名色是识的条件。 ↩
-
五盖(pañca nīvaraṇā):培育定力和观禅的主要内在障碍。见上文,第八章第三篇。 ↩
-
见第440页(第八章,注147)。 ↩
-
关于五蕴,见第22, 306–7页,以及第九章第四篇(1)(a)-(e)。 ↩
-
五蕴的生起与坏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1) 通过它们依赖其条件而生起和止息(见第九章第四篇(1)(a));以及(2) 通过它们可辨识的生、变、灭(见《相应部》22:37–38)。这两种方式并非相互排斥,但在概念上可以区分。 ↩
-
关于六内入处,见第309–11页以及第九章第四篇(2)(a)-(e)。 ↩
-
结缚是将感官官能与其对象绑在一起的欲与贪(chandarāga);见《相应部》35:232。 ↩
-
关于七觉支,见第八章第九篇。 ↩
-
巴利语义注详细说明了导致七觉支成熟的条件。见Soma Thera,《念住之道》,第134–149页。 ↩
-
《长部》中较长的《大念住经》定义并详细阐述了四圣谛的每一谛。亦见《中部》141。 ↩
-
究竟智(aññā)是阿罗汉的解脱之智。不还(anāgāmitā)是证得不还者的状态。 ↩
-
从这一点开始,此经与《安般念经》(《中部》118)的第二部分紧密对应,该经的第一部分是安般念指导的序言。第一个四法组与刚才在《念住经》“身随观念住”部分中关于安般念的段落完全相同。 ↩
-
“心行”(cittasaṅkhāra)是想和受;见《中部》44 (I 301) = 《相应部》41:6 (IV 293)。 ↩
-
Vism 289; Ppn 8:233:“解脱心”指通过初禅从诸盖中解脱,通过逐次证得更高禅那从较粗的禅支中解脱;以及通过观智从认知扭曲中解脱。 ↩
-
Vism 290–291; Ppn 8:234–37:“随观无常”(aniccānupassī)是将五蕴视为无常,因为它们经历生灭与变化,或因为它们经历刹那坏灭。这个四法组完全涉及观禅,与其他三个不同,后三者可以从止禅和观禅两方面来解释。“随观离贪”(virāgānupassī)和“随观灭尽”(nirodhānupassī)既可以理解为对现象刹那坏灭和止息的观禅,也可以理解为实现涅槃作为贪欲的消退(virāga,离贪)和诸行的止息的超世间道。“随观舍遣”(paṭinissaggānupassī)是通过观禅舍弃(pariccāga)或断除(pahāna)烦恼,并通过证得道而进入(pakkhandana)涅槃。 ↩
-
Spk:作意实际上不是受,但这是教法的一个标题。在此四法组中,第一句以喜(非受)为标题间接谈及受,第二句则直接提及乐(=乐受)。在第三和第四句中,受包含在心行中。 ↩
-
Spk:以智慧见到等。此处,“渴望”即欲欲盖;以“忧恼”示嗔恚盖。此四法组仅依观禅而说。此二盖为五盖之首,是法随观念住的第一部分。故他说此以示法随观念住之始。所谓“断除”,意指能导致断除的智,例如,人以无常随观断除常想。以“以智慧见到”之语,他如此开示诸观禅之次第:“以一观智(他见到)由无常、离贪、灭尽及舍遣等诸智所构成的断除之智;而此(他见到)又藉由另一(观智)。”他是以舍心密切观察者:据说人以舍心观察(已)沿道而行的心[Spk-pṭ:对已正确地行于中道上的培育之心既不策励也不抑制],并通过统一的呈现[Spk-pṭ:因为当心已达一心时,于此方面已无事可为]。人“以舍心观察”所缘。 ↩
-
念觉支(Satisambojjhaṅga)。Bojjhaṅga由bodhi + aṅga复合而成。在《相应部》46:5中,它们被解释为导向觉悟的要素。用于描述培育每一觉支的三个词组,可以理解为描绘了三个相继的发展阶段。“他生起”是其初始的生起;“他培育”是其逐渐的成熟;以及“它通过培育而圆满”是其顶峰。 ↩
-
择法觉支(Dhammavicayasambojjhaṅga)。在《相应部》46:2 (V 66)中,据说此觉支生起的“资粮”是频繁地如理作意善与不善的心所法,应谴责与不应谴责的状态,劣与胜的状态,以及黑暗与光明及其对应之状态。虽然此觉支被等同于般若或智慧,但上述段落表明,其初始功能是辨别随着念住的加深而变得明显的善恶心所法。 ↩
-
舍利弗(Sāriputta)是佛陀的两位上首弟子之一,是智慧第一者。其传记见Nyanaponika与Hecker合著的《佛陀的大弟子》第一章。 ↩
-
“我作”(ahaṅkāra)是身见的作用;“我所作”(mamaṅkāra)是渴爱。根源的我慢是“我是”慢(asmimāna),因此“我慢随眠”也对“我作”负责。 ↩
-
想受灭尽定(Saññāvedayitanirodha)。亦称为灭尽定(nirodhasamāpatti),此为一种特殊的禅定,据说只有不还者和阿罗汉才能证得。顾名思义,它涉及想与受功能的完全止息,根据义注,也包括识及其所有相应心所的止息。根据义注系统的详细讨论,见《清净道论》702–9;Ppn 23:1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