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杰德·麦肯纳的戏剧(梦境三部曲#2)
杰德·麦肯纳, 实相与解构 ·Index
Play: A Play by Jed McKenna - Jed McKenna
戏剧:杰德·麦肯纳的戏剧(梦境三部曲#2) - 杰德·麦肯纳 - 摘要
人生不过是一场荒诞的游戏,而你,既是演员也是观众,唯一的出路是看穿这场戏剧的虚伪:所有可见之物,不过是纸板面具。囚犯如何能触及外面的世界?除非他能冲破墙壁。对我而言,白鲸就是那堵墙!
编辑前言:我们该如何理解这部“戏剧”?
如果你熟悉杰德·麦肯纳,你对这部新作的疑问可能和我们最初一样:一部戏剧?说真的?这是一部真正的舞台剧,还是仅仅借用了戏剧的形式?我们充满了好奇,却得不到直接的答案。它就是它本身。
如果你不熟悉杰德,可以先了解一下他的风格,看看你将要踏入的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书名《戏剧》(Play)本身就蕴含了多重优雅的含义。它既指作品本身是一部戏剧,也暗指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戏剧——一场零和游戏。在这场游戏中,输赢无关紧要,如何参与也无关紧要。表演本身毫无意义,但我们依然在表演。戏剧,即使严肃,也带着玩乐的性质;即使玩乐,也如生命本身一般严肃。说到底,一切皆是游戏。
为了解释剧中缺乏连贯故事和丰满角色的现象,我们想将其归类为“荒诞派戏剧”,但它又不完全是。荒诞派戏剧是从“闭着眼睛”的视角,荒诞地审视存在。而杰德的视角是“睁开眼睛”的。因此,我们不妨称之为“超荒诞主义”或“后荒诞派元戏剧”。
如果你没有读过杰德的三部曲,能看懂这部戏剧吗?可以,但理解的深度会稍逊一筹。《戏剧》值得反复阅读和品味,无论你是否熟悉他的其他作品,其意义都会在细节和整体中逐渐为你展开。剧中的朱莉(Julie)正处于一场旷日持久的自我消解危机中,与杰德进行着一场单向对话。亚哈船长(Ahab)则处于一种“唯有在沉静中才能理解自身的狂野疯癫”的状态。而神谕(Oracle)究竟是谁,则取决于你的解读。
杰德·麦肯纳向来更倾向于摧毁问题,而非回答问题。因此,《戏剧》更像是一连串的“提问”而非“解答”。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场自我探寻之旅的阶段性展示。七个独立的场景,每一个都将我们更深地带入内在旅程。前面的场景提出问题,后面的场景则审视那些提问者;它向我们展示、承诺,也警告我们——一场诚实而不懈的探寻,究竟会将我们引向何方。
但正如杰德曾经问过的:谁又真的想去这条路真正通往的地方呢?在这段旅程中,“你是谁”这个问题,随着你迈出的每一步而改变。关键在于,迈出下一步。
最终,《戏剧》就是它本身。或者不是?也许《戏剧》是一场审视生命旅程的寓言,也许它只是一部轻松俏皮的小剧本。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或者两者皆非。当然,最终,《戏剧》就像生活,像任何事物一样,对你而言,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第一幕:双子座 (Gemini)
开场音乐是童声循环吟唱的摇篮曲:《摇啊摇,宝贝》
场景与角色
- 兄妹(Bro & Sis):一对刚出生一天的龙凤胎,被绑在汽车安全座椅里,正从医院开车回家。他们戴着粉色和蓝色的帽子,手舞足蹈。
- 其他角色:父亲的声音、母亲的声音、哥哥的声音、GPS导航的声音。
剧情摘要
兄妹俩在回家的车里醒来。哥哥(Bro)试图搭讪妹妹(Sis),自报是双子座,却被告知两人是双胞胎。他们迅速进入了典型的兄妹斗嘴模式,但随即又冷静下来,开始了一场关于生命本质的超现实对话。
“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各自的角色,”哥哥说。 “是的,仿佛我们是预设好程序的。”妹妹回应。 “或者像是活在一部戏剧里,剧本早已写好,结局早已注定。”
他们戏谑地想要“打破角色”,成为“叛逆宝贝”,甚至还编了一首 70 年代警匪片风格的主题曲。但很快,他们意识到在学会上厕所之前,谈论叛逆还为时过早。
透过车窗,他们观察着这个陌生的世界,用婴儿的视角给事物命名——一只鸟被哥哥称为“消防车”。他们讨论着前排的“大脑袋”(父母)和那个不停问“为什么”的五岁“小脑袋”(哥哥)。他们给自己取了“臭屁裤先生”和“便便裤公主”这样滑稽的名字。
对话迅速转向深刻的哲学议题。他们探讨生命的意义、未来的可能性,以及自己是否拥有自由意志。
“你觉得我们有自由意志吗?”妹妹问。 “我喜欢这么认为。”哥哥回答。 “人人都喜欢这么认为,但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我喜欢认为我在思考,但我不认为我真的在思考。”
妹妹在出生第一天就感受到了存在的绝望和虚无。她引用加缪的话说:“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是自杀。”她认为生命毫无意义,充满了干扰注意力的娱乐,但底层却是一片黑暗,毒害着每一个快乐的瞬间。
哥哥则扮演了乐天派的角色。他认为妹妹的悲观为时过早,并用一首自编的、关于加缪如何解决自杀问题的滑稽歌曲来调侃她。他将生命比作一个盛大的嘉年华,鼓励妹妹放下对意义的幼稚需求,尽情“玩乐”。
“在这个嘉年华里,没有一个角色会被空置。我们的故事必须被讲述。”哥哥说。 “我们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是必然的。”妹妹回应。
他们讨论了是被困在一个“魔法盒子”里,还是拥有真正的自由。他们认为,即使被困住,也可以把盒子的墙壁画成美丽的风景,或者干脆把“天花板”命名为“自由天花板”,通过重新定义来获得自由感。
最终,他们决定一个扮演“角色”(妹妹),一个履行“功能”(哥哥),并在最后比较心得。哥哥将成为妹妹表演的观众,一个“不可移动的盆栽植物”,对应妹妹那“永不停歇的鲨鱼”。
当妹妹再次陷入存在的孤独与痛苦时,哥哥揭示了自己黑暗的一面:他预见自己将成为一个“怪物”,会犯下罪行,背叛爱,让亲近的人受苦。他告诉妹妹,这个嘉年华的本质就是“碰撞与燃烧”,他会在这里制造一场大混乱。
妹妹听后,反而找到了出路。她明白了,这个嘉年华的规则就是“时刻闭上眼睛”。她决定不再去“看”,而是闭上眼睛,尽情玩乐,尖叫欢笑,用更卖力的表演来对抗真相的浮现。
剧终时,两个婴儿再次陷入疯狂的舞蹈,然后沉沉睡去。幕布落下。
(幕间休息 1)
一对年轻男女(Guy & Girl)分别在剧场两侧打电话,他们是来看戏的约会对象。女孩觉得男孩带她来看戏剧有点“怪”,不确定这戏在讲什么。男孩也同样困惑,但他对剧中“关于自杀的歌”和“婴儿与乳房”的情节还有些印象。他们的对话充满了对这部“哲学剧”的困惑和疏离感,为下一幕做了铺垫。
第二幕:触碰小指 (Pinky Touch)
转场音乐是童声吟唱的《玫瑰花环》
场景与角色
- 老兵(Mate):年长的守卫。
- 新兵(Lad):年轻的守卫。
- 囚犯:被捆绑并蒙住双眼,全程沉默。
- 护士:衣着整洁、乐观开朗,与环境格格不入。
- 场景:一间潮湿的、地牢般的军事审讯室,窗外是战争的火光与声响。
剧情摘要
老兵和新兵正在看守一名沉默的囚犯。新兵感到极度无聊,提议玩各种游戏,从掰手腕到猜谜,但都被老兵以“我们的工作是看守囚犯”为由拒绝。最终,老兵同意玩一个名为“触碰小指”(Pinky Touch)的荒诞游戏,规则不明,但两人玩得异常投入。
新兵对囚犯心生怜悯,想给他一些食物。老兵严厉地制止了他,描绘了审讯官即将对囚犯施加的种种酷刑:拔指甲、敲碎关节、电击……他告诉新兵,他们唯一能为囚犯做的“善事”,不是喂他食物,而是在他脑袋里开一枪。
这段对话引出了关于“公平”和“黄金法则”的争论。老兵认为,在战争这种黑白分明的环境下,哲学和道德准则毫无用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被修改为“在别人对你动手之前,先对他们动手”。
新兵则从房间里摇摇欲坠的行军床,联想到了所有“非自然”事物的必然崩溃。他将大坝比作一种对河流自然流动的“侵犯”,认为所有违背自然秩序的人造物——大坝、建筑、飞机——最终都将崩塌。他看着窗外的战火,断言他们正处于崩溃的最后阶段,一切都将化为灰烬。
老兵反驳道,人类的自然秩序或许就是“侵犯自然的自然秩序”。他认为,即使这些“反重力装置”无法永存,但它们在存在期间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就像他们作为士兵一样。
一位护士轻快地走进房间,用欢快的语调描述着战争的惨状:大规模伤亡、可怕的伤口、因吗啡耗尽而响彻云霄的惨叫。她总结说:“总而言之,战争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她也感叹,当战争结束,当恐怖和疯狂被锁进书本,他们这些“认识战争的人”又将成为谁呢?
护士离开后,老兵突然陷入一种癫狂的状态。他声称自己看到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模式”(Pattern)。他拉着新兵,指着地板的不同区域,让他比较异同。
“它们完全一样,只是不同。”新兵说。 “就是这个!模式!这就是关键!”老兵激动地喊道。
老兵解释说,他顿悟到宇宙中并非存在无数种模式,而只有“唯一的模式”。一旦学会感知这个模式,人一生中就只需要做一个决定:是“顺从”(with)还是“反抗”(against)。他建议新兵,在当前的环境下,“反抗”是糟糕的选择,最明智的做法是“顺从”——安分守己,履行职责,不要多管闲事。
新兵被老兵的“模式论”搞得心烦意乱,躺下睡着了。等他醒来,老兵告诉他,审讯官已经来过了。新兵大惊失色,因为他没有听到任何惨叫,囚犯也完好无损。
老兵描述了审讯官的来访:他悄无声息地走进来,站在囚犯身后许久,然后俯身只问了一个问题,便转身离去,甚至没有等待答案。
“他问了什么?”新兵急切地追问。 老兵回答:“他问,‘为何是有,而不是无?’(Why something instead of nothing?)”
这个问题让新兵彻底崩溃了。他无法理解,在血流成河、世界濒临毁灭的战争中,审讯官——他们逆转战局的最后希望——竟然会问出如此抽象、荒谬的哲学问题。他认为这简直是“疯狂之上的疯狂”。他躲在行军床后,语无伦次地表达着自己的绝望和困惑。
老兵则平静地引用《圣经》说:“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新兵在绝望中怀疑老兵就是审讯官本人。老兵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我也经常问自己这个问题。”
最后,新兵放弃了思考,邀请老兵再玩一局“触碰小指”。两人跪在地板上,重新开始了他们那荒诞的游戏。
(幕间休息 2)
年轻男女再次打电话。女孩觉得剧情越来越“诡异”,开始担心男孩的品味。男孩则对“模式”和“为何是有,而不是无”的问题产生了些许思考。他们对这部剧的感受开始出现分歧。
第三幕:游行 (Parade)
转场音乐是童声循环吟唱的《永不结束的歌》
场景与角色
- 丈夫与妻子(Husband & Wife):一对七十岁左右的肥胖夫妇,衣着几乎一模一样(夏威夷衬衫、短裤、凉鞋配袜子),坐在折叠椅上观看游行。
剧情摘要
一对老夫妻正在观看一场小镇游行。他们讨论着这是他们一起观看的第几百场游行。丈夫认为,他们实际上是把“同一场游行看了四百遍”。他觉得人生太长了,充满了无尽的重复,并感叹自己每天都在读着“同一份报纸”。
妻子则试图享受当下,不断提醒丈夫要“品味这一刻”。她私下里独白说,丈夫虽然爱抱怨,但本质不坏。他总觉得自己有一些深刻的哲学见解,但其实都来自T恤和保险杠贴纸。
丈夫则认为妻子不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他觉得人生的一个问题在于,你不知不觉就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轨道”,而一旦走上这条轨道,一切就结束了。他后悔错过了生命中某个“决定性的时刻”,如果能回到过去,他会告诉年轻的自己:“不要走上正确的轨道。”
他幻想自己能做出惊世骇俗之举来“留下印记”——比如脱光衣服,身上涂满粪便,加入游行队伍。他认为,在这个时代,只有制造一场混乱,才能证明自己曾经存在过。
妻子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她独白说,丈夫不理解“扮演角色”和“履行功能”的区别。人人都想当英雄,但如果都是英雄,谁来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观众呢?她认为,在台下观看别人屠龙救公主,然后回到自己舒适的小盒子里“品味”,其实是更美好的事。
丈夫站起来,大声引用《圣经》中的段落,宣称“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切都是虚空,都是捕风”。
此时,妻子突然像被附身一般,站起来发表了一段关于“模式”的演讲。她用裁缝为男士量身裁衣时问“先生的‘习惯’是偏左还是偏右?”(Which way does the gentleman dress?)这个隐喻(此为裁缝询问男士裤子剪裁时,关于其生理习惯的委婉说法),来解释一个人的天性是固定的,无法轻易改变。
她警告说,如果所有人都违背自己的天性,那么“自然秩序”就会被侵犯,世界将陷入混乱,“模式本身将被扰乱”。
但她随即揭示了谜底:“模式是永远不可能被扰乱的,亲爱的。因为任何扰乱本身,都会立刻成为新的模式。你看,这多聪明?”
丈夫被妻子的这番话惊得目瞪口呆。妻子恢复了常态,递给他一块甘草糖,温柔地说:“品味这个吧。游行的小丑来了。” 两人又像最初那样,兴高采烈地看着游行。
(幕间休息 3)
年轻男女再次打电话。男孩对剧中“裁缝的问题”感到困惑。女孩则觉得这出戏越来越荒唐,开始抱怨男孩带她来看戏的决定。
第四幕:辩论 (Debate)
转场音乐是童声吟唱的《矮胖子》
场景与角色
- 主持人:三十多岁的女性。
- 科学(Science):身穿白大褂、仪表堂堂的男性。
- 宗教(Religion):身穿牧师长袍、同样仪表堂堂的男性。
- 哲学(Philo):一个名叫佩妮(Penny)的15岁高中女生。
- 场景:一个非正式的辩论会舞台,主题是“现实的本质”。
剧情摘要
一场关于“现实本质”的辩论即将开始。代表宗教和科学的分别是两位德高望重的教授。然而,代表哲学的帕拉多夫斯基教授并未到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名叫佩妮的高中二年级女生。
佩妮解释说,她因为读了柏拉图关于“我们如何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的论述而产生了疑问。她向老师和大学教授提问,但都遭到了敷衍和驱赶。最后,不耐烦的帕拉多夫斯基教授把辩论会的邀请函给了她,让她代为出席。
尽管科学和宗教代表强烈反对,主持人还是允许佩妮加入了辩论。
辩论开始后,宗教声称现实是上帝创造的,而科学则认为现实由不可改变的法则支配。当轮到佩妮时,她说自己没有任何观点,只是来提问的。
她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何是有,而不是无?” 宗教的回答是:“因为上帝。” 科学的回答是:“怎么可能是无?现实就是有。”
佩妮紧接着抛出了核心问题:“但现实是真实的吗?我们如何知道自己不是在做梦?我们如何能‘知道’任何事?”
这个问题让科学和宗教陷入了困境。他们承认无法从根本上证明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科学代表承认,他所谓的“知识”其实是“被证成的个人信念”(justified subjective belief),而非客观真理。
这个承认立刻引发了宗教的攻击,他指出,如果科学无法证明任何事,那它本身就是一种“信仰体系”。两位代表随即陷入了长久以来典型的、毫无结果的争吵,互相攻击对方的体系。
他们联合起来,试图用权威和实用性来压倒佩妮: “科学能把人送上月球,哲学行吗?” “人们会在酒店房间里放哲学书吗?” “你难道要找个哲学家来主持你的婚礼吗?”
他们指责佩妮用一个简单的问题扰乱了他们之间“和谐”的辩论生态。佩妮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所谓的辩论只是争吵,他们的体系都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未经证实的基础上——即“所见即所得”(everything is as it seems)。
她把“现实”放上了审判席,挑战这个最基本的假设:“我们都说‘它就是它本来的样子’(it is what it is),但,是吗?”
最终,两位代表承认,他们无法回答佩妮的问题。科学承认,他无法证明光、时间、空间甚至物质的存在,但他认为科学的职责是处理我们能处理的事情。宗教则表示,任何科学或哲学都无法动摇他内在的信仰之光。
辩论以佩妮的独白结束。她意识到,她永远无法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只梦见自己是女孩的蝴蝶,但“知道自己一无所知”,或许本身就是一种“知”。
辩论在一片混乱和未解的疑问中结束。
(幕间休息 4)
年轻男女再次打电话。男孩被佩妮的简单问题所震撼,开始反思,甚至想去“读本书”。女孩则觉得这一切很无聊,她认为科学就是对的,不该被取笑。两人之间的思想差距越来越大。
第五幕:无我 (Anatta)
转场音乐是童声吟唱的《整夜》
场景与角色
- 朱莉(Julie):三十岁左右的女性,憔悴、瘦削、精神恍惚。
- 场景:一间凌乱的乡间小屋,壁炉里燃着火。桌上堆满了纸张、水瓶和咖啡杯。
剧情摘要
这是全剧唯一一幕独角戏。朱莉正经历着一场剧烈而残酷的自我瓦解过程。她时而呕吐,时而疯狂地在纸上写画,又撕碎扔掉,咒骂自己是“傻瓜、懦夫、骗子”。
她与一个看不见的、被她称为“他”(暗指杰德·麦肯纳)的人对话。她回忆起“他”的教诲:“小步前进”、“不要抗拒”、“痛苦来自抗拒”。她挣扎着去实践这些教诲,但过程极其痛苦。
“我正在一片一片地剥掉自己的皮肤,这太折磨人了,我怎么能不抗拒?”
但她也体验到了某种解放。她发现,过去那些她曾无比执着的东西——事业、外貌、男友、金钱——如今都变得无关紧要,仿佛“被冲走了一样”,甚至记不起当初为何那么在乎。
她的精神状态在崩溃与清醒之间剧烈摇摆。前一秒,她还蜷缩在地板上,像个孩子一样哭喊着“妈妈,我想回家”;后一秒,她又重新振作,意识到自己“宁愿死,也不愿回到过去的生活”。她烧掉了自己写的“宣言”,那是她试图解释自己为何清醒而全世界都疯了的长篇大论。
她意识到,“失败是我的优势,死亡是我的优势”。这种“向死而生”的态度,让她体会到了真正的“臣服”——从希望、欲望和期待中解脱出来。
她不断地给“他”写电子邮件,记录下自己疯狂而清醒的思考。她问自己是否疯了,结论是:“我绝对、确定地相信,我是清醒的,而其他所有人都疯了。”
电话铃声响起,她知道是家人打来的。她挣扎着想要伪装成一切正常,但最终在一次想象中的通话里,她对母亲吼出了真相:她正在经历一场无法回头的“精神崩溃”,她正在“像割掉肿瘤一样,把你从我心里切除”。
风暴再次来临。她感到体内的能量在翻涌,无法平息。她意识到自己必须面对最不想面对的东西。她不再逃避,而是选择直面。
她把自己变成了一名“战士”,宣布“全员进入战斗岗位”。她脱掉外衣,露出运动内衣,将头发扎紧,进入一种狂喜的战斗状态。
“通往我既定目标的道路,铺设着铁轨,我的灵魂注定要在其上奔驰。”她反复念着这句话。
她知道,这条路的终点是彻底的毁灭,包括毁灭那个指引她的“他”。但在此刻,尽管痛苦、失落、结局注定,她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
在狂笑中,她举起双臂,宣告自己的胜利:“我已经赢了!”
(幕间休息 5)
男孩被这一幕深深震撼,感到“一头雾水”。他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灵魂是否也“涂着一层黑色的狗屎”。女孩则完全无法理解,感到厌烦。
第六幕:费达拉 (Fedallah)
转场音乐是童声吟唱的《鲸鱼是个小丑》
场景与角色
- 亚哈(Ahab):独腿船长,形象憔悴、饱经风霜。
- 斯达巴克(Starbuck):大副,年轻、勇敢、正直。
- 费达拉(Fedallah):一个手持鱼叉、双眼发红的恶魔般身影,潜伏在暗处。
剧情摘要
这一幕是对赫尔曼·麦尔维尔小说《白鲸》的重新编排和演绎。亚哈船长在甲板上踱步,思考着命运与自由意志。他感叹自己四十年来在海上追逐,究竟是受何种“无名的、不可思议的、超凡之物”所驱使。他质问:“是亚哈就是亚哈吗?上帝啊,是我在抬起这条手臂吗?”
斯达巴克悄悄走上甲板,他准备杀死疯狂的亚哈,以拯救全船人的性命。然而,当他用枪对准亚哈的后脑时,亚哈却转过身,向他展示了自己脆弱的一面,谈论着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斯达巴克心软了,放下了枪,恳求亚哈放弃追逐白鲸,返航回家。
亚哈瞬间又变得坚硬而决绝。他推开斯达巴克,宣告自己绝不回头,追杀白鲸是他“最渴望的健康”。
斯达巴克指责他疯狂地向一头“凭着最盲目的本能”攻击他的“哑巴畜生”复仇。
亚哈则道出了他那著名的宣言:“听着,斯达巴克,还有更深一层。所有可见之物,不过是纸板面具。如果人要攻击,就必须戳穿那面具!囚犯如何能触及外面的世界,除非他能冲破墙壁?对我而言,白鲸就是那堵墙!”
他宣告自己是“命运的代理人”,他只是在“奉命行事”。这场追逐是“亿万年前就已排练好的”。
斯达巴克绝望地离去。亚哈独自面对风暴,向天空咆哮,他将鱼叉指向天空,宣布对上帝的“崇拜就是反抗”。他从费达拉手中接过鱼叉,再次念诵起那句贯穿全剧的台词:“通往我既定目标的道路,铺设着铁轨,我的灵魂注定要在其上奔驰。”
(幕间休息 6)
男孩和女孩再次打电话,对刚才的《白鲸》改编版发表评论。他们因为“Dick”(迪克,也是男性生殖器的俗称)这个词的发音而产生了滑稽的误会。男孩似乎对剧中的深层含义有所感悟,而女孩则认定这不过是一堆“拼凑不起来的碎片”。
第七幕:德尔斐 (Delphi)
转场音乐是童声轮唱的《划船歌》
场景与角色
- 男人(Man):身穿白色医院病号服,赤脚。
- 神谕(Oracle):身披面纱,慵懒地躺在王座般的石头躺椅上。
- 场景:一片荒凉的古代石头废墟。一块断裂的拱门上刻着“认识你自己!”。空中悬挂着几片破旧的面纱,背景中,一栋豪宅的影像投射在一片面纱上,一个标有“出口”的门投射在另一片完好的面纱上。
剧情摘要
一个男人在废墟中醒来,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确定自己是谁。一个神秘的声音(神谕)开始与他对话。神谕的回答总是模棱两可,充满禅意。
男人问这是哪里,神谕说:“它看起来是什么,它就是什么。” 男人问神谕是谁,神谕说:“我是你听到的那一位。”
男人发现刻有“认识你自己!”的断裂石块,神谕评论说这“很讽刺”。男人想要离开,神谕指了指远处的豪宅影像和“出口”门影像,让他自己选择。
男人被困在神谕的谜语中。他坚持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是”,而神谕则告诉他:“没有‘是’,只有‘看似是’(There is no is, there is only seems)。” 神谕告诉他,他所看到的豪宅,不过是“投射在破旧面纱上的影像”,他所有的记忆也是如此。
神谕进一步揭示,宇宙的本质不是“有”或“无”(因为“无”根本不存在),而是“模式”。
“那么我算什么?”男人问。 “似乎是模式。或许还是模式的观察者?”神谕回答。
男人回忆起自己曾经的生活,充满了人、事、物,一个完整的世界。神谕告诉他,如果想回去,就走向那栋豪宅。
在做出选择的关头,男人突然进入一种出神状态。他看到了自己完整的一生,每一个细节都清晰无比。他明白了,自己的一生就是一条“优雅的曲线”,通往此刻此地。他意识到,自己一直在进行一场“伟大的回归之旅”。
他从出神中醒来,记忆消失了,但他不再迷茫。他明白了“认识你自己”的石块为何会断裂——因为它不是一个终点。
神谕最后向他揭示了真相:他们正身处一个“剧场”,一个“魔法盒子”里。豪宅是投影,面纱是虚无,神谕的声音也只是他脑中的声响。那个“出口”门,就是剧院的出口。
“你想要退出这场演出吗?”神谕问,但又说,“别回答!你的愿望无关紧要。你以为还有选择吗?”
男人终于明白了。他走向那个标着“出口”的最终面纱。他知道自己不能回去,也不能停留,唯一的路就是前进。他撕开面纱,走了过去。
神谕的身影也随之消失。
黑暗中,传来一个小男孩的声音:“妈妈,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剧终时,那对年轻男女从舞台两侧跑出来,扔掉手机,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或许是因为这部戏剧太过精彩而疯狂地爱上了对方,或许只是像沉船的幸存者一样,在绝望和解脱中寻求慰藉。
(全剧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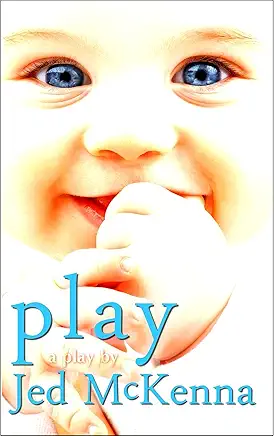 |
本文为书籍摘要,不包含全文如感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 |

